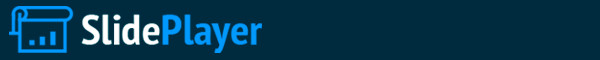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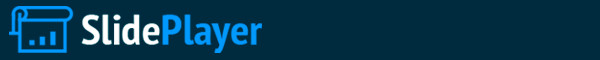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中国文学批评史 第五编 明 代
绪 论 明代前期诗文批评与台阁体 前后七子的复古诗文理论与唐宋派 公安、竟陵的“性灵”等说与陈子龙的忧时托志诗论 戏曲批评的发展和繁荣 绪 论 明代前期诗文批评与台阁体 前后七子的复古诗文理论与唐宋派 公安、竟陵的“性灵”等说与陈子龙的忧时托志诗论 戏曲批评的发展和繁荣 小说批评的巨大发展
第一章 明代的诗文批评
第一节 明初的诗文批评 宋濂 刘基 高启 高棅 方孝孺 李东阳
宋 濂 由元入明、理学、政教 (一)明道致用 (二)宗经师古
高棅 唐诗品汇 推崇盛唐,标举体格(复古) 分期的命题链:文学与世运*
隋氏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 隋氏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大历贞元之诗是也;四变而为晚唐,元和以后之诗是也。(高棅《唐诗品汇》卷二十) 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入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严羽)
诸体集内定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傍流诸品目者,不过因有唐世次文章高下而分别诸卷,使学者知所趋向,庶不惑乱也。 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傍流,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如陈子昂与太白列在正宗,刘长卿、钱起、韦柳与高岑诸人同在名家者是也。
第二节 李梦阳、何景明 弘治正德年间,政治腐败 理学与八股文 第二节 李梦阳、何景明 弘治正德年间,政治腐败 理学与八股文 杨慎: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 李何复古:宋之前有高格、逸调、真情之诗文
李梦阳的诗文理论 (一)贵情 诗贵宛不贵险,贵质不贵靡,贵情不贵繁,贵融洽不贵工巧。……三代以下汉魏最近古。 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
(二)真诗在民间 李子曰:“曹县盖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 。”今真诗乃在民间。而文人学子,顾往往为韵言,谓之诗。夫孟子谓《诗》亡然后《春秋》作者,雅也。而风者亦遂弃而不采,不列之乐官。悲夫!’”李子曰:“嗟!异哉!有是乎?予尝耹民间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声哀,其调靡靡,是金、元之乐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古者国异风,即其俗成声。今之俗既历胡,乃其曲乌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辨也。且子之耹之也,亦其谱,而声音也,不有卒然而谣,勃然而讹者乎!莫之所从来,而长短疾徐无弗谐焉,斯谁使之也?”李子闻之,矍然而兴曰:“大哉!汉以来不复闻此矣!”
(三)诗法 又谓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也,实天生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
五古 夫追古未有不先其体者也。 《选》体五古 唐体五古 汉魏风雅 受近体律诗影响 正宗 旁支 夫五言者不祖汉则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即当效陆、谢矣。(李梦阳) 盖诗虽盛称于唐,其好古者自陈子昂而后, 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区者,犹未尽可法也。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 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何景明) 五古 《选》体五古 唐体五古 汉魏风雅 受近体律诗影响 正宗 旁支
景明仕官时,尝与学士大夫论诗,谓三代前不可一日无诗,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代以后,言治者弗及诗,无异其靡有治也。然诗不传,其原有二:称学为理者,比之曲艺小道而不屑为,遂亡其辞;其为之者,率牵于时好而莫知上达,遂亡其意。辞意并亡,而斯道废矣。故学之者,苟非好古而笃信,弗有成也。 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
李何之争 (一)诗法之争 (何景明)
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有意必二,此予之所谓法,圆规而方矩者也。(李梦阳) (何景明)
(二)模仿与创新 献吉兢兢尺寸,非规矩不由;先生志在运斤斲轮,务底于化。于时,主典则者张献吉,主神解者附先生。(汪道昆《何光生墓碑》) 追昔为诗,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物造,不仿形迹。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仆之愚也。(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
古之工,如捶,如班,堂非不殊,户非同也,至其为方也,圆也,弗能舍规矩,何也 古之工,如捶,如班,堂非不殊,户非同也,至其为方也,圆也,弗能舍规矩,何也?规矩者,法也。仆之尺尺寸寸者也,固法也……作文如作字,欧、虞、颜、柳,字不同而同笔。笔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长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势也,字之体也,非笔之精也。精者何也?应诸心而本诸法者也。(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
(三)粗豪与俊逸 薛蕙: 海内论诗伏两雄,一时倡和未为公。 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 何景明: 子美辞固沉著,而调失流转。……至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与? 李梦阳: 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义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调,沉著雄丽,清峻闲雅者才之类也。
第三节 唐宋派 诗:初中唐、六朝 文:唐宋。(文学向理学、包括心学切换) 向理学的回归本就意味着向唐宋文的靠拢
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领者,莫如韩、欧、苏、曾诸名家。今观诸贤尚有薄宋人之心,故其文如此。吾尝谓自我倡明此道以来,海内英俊之士必有兴者。每以语(李)舜臣,渠则应曰:“未之见也。”今观诸作亦尚如此,信乎舜臣之言矣。自七月作数文以后,与舜臣出游,及退而观书, 未暇有作,只作《刘涵江表》、《丘集斋传》, 聊付汝观之。然以今好尚,制作如彼,见吾所为文,得不以为宋人腐烂冗俗之病而大笑丑诋之乎?不知此正所谓《史》、《汉》而兼根《六经》也。何由与诸贤一详论之。决不可示人,徒资噱摈也。
三代以下之文,莫有如南丰(曾巩);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 (邵雍)者。(唐顺之)
第四节 李攀龙、王世贞及其他 嘉靖时,海内稍驰骛于晋江(王慎中)、毗陵(唐顺之)之文,而诗或为台阁也者,学或为理窟也者。(李)于鳞始以其学力振之,诸君子坚意倡和,迈往横厉,齿利气强,意不能无傲睨。”(王世懋《贺天目徐大夫子与转左方伯序》)
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
第五节 公安派与竟陵派 公安派及其与李贽、徐渭的关系 代有升降,法不相沿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袁中道的修正理论
一、公安派及其与李贽、徐渭的关系 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于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 掇:duó,拾取。
其人(李贽)不能学者五,不愿学者有三:公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汩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脔刀狼藉,不愿学者三矣。(袁中道《李温陵传》) 嬖:bì 宠爱 汩:ɡǔ
二、代有升降,法不相沿 公安派的命题链: 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文长、义仍,崭然有异,沉痼滋蔓,未克芟薙。……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勋宏道》)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袁宏道《叙小修诗》)
三、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唐宋派的“洗涤心源”说 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来,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番来复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
公安派的“师心”说 (小修)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袁宏道《序小修诗》) 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与张幼于)
四、袁中道的修正理论 当余少年盛气之时,意不可一世士。见乡里之铢持寸守者,意殊轻之,调笑玩嫚,见于眉睫。中年以来,饱历世故,追思曩日所怀,可愧非一。吾辈常轻谈天下事,以为无不可为,而其后百不一雠。 (袁宏道《寿刘起凡先生》)
嗟乎,自宋、元以来,诗文芜烂,鄙俚杂沓。本朝诸君子出而矫之,文准秦、汉,诗则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后也、剽窃雷同,如赝鼎伪觚,徒取形似,无关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应酬格套之习,而诗文之精光始出。…… ……至于一二学语者流,粗知趋向,又取先生少时偶尔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譬之百花开而棘刺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埌(lang4)之水亦流,乌焉三写,必至之弊耳,岂先生之本旨哉!
五、竟陵派 尝试论之,诗文气运,不能不代趋而下,而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然其变有穷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变无穷也。操其有穷者以求变,而欲以其异与气运争,吾以为能为异,而终不能为高。其究途径穷,而异者与之俱穷,不亦愈劳而愈远乎?此不求古人真诗之过也。 今称诗不排击李于鳞,则人争异之,或以为著论驳之者自袁石公始。……石公恶世之群为于鳞者,使于鳞之精神光焰不复见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称诗者,遍满世界,化而为石公矣,是岂石公意哉?(钟惺)
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无以服其心,而又坚其说以告人曰,千变万化不出古人。问其所为古人,则又向之极肤极狭极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诗归序》) 眼见今日牛鬼蛇神、打油、钉铰,遍满世界,何待异日,慧力人于此尤当紧着眼。(公安派末流之弊)
其(指宏道)识已看定天下所必趋之壑,而其力己暗割从来自快之情。予因思古今真文人何处不自信,亦何尝不自悔。当众波同泻、万家一习之时,而我独有所见,虽雄裁辨口,摇之不能夺其所信。至于众为我转,我更觉进,举世方竞为喧传,而真文人灵机自检,已遁之悔中矣”。“夫公之妙于悔,何待公言哉!细心读《破砚集》,又似悔《潇碧》矣;细心读《篙华游稿》,又似悔《破砚》矣。今察公续稿,其文章中卓大而坚实者,又似为古今人俱下一悔脚也”。(谭元春《袁中郎先生续集序》)
惺与同邑谭子元春忧之。内省诸心,不敢先有所谓学古不学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谓吾之说,非即向者千变万化不出古人之说,而特不敢以肤者狭者熟者塞之也。
古称名士风流,必曰门庭萧寂、坐鲜杂宾,至以青蝇为吊客,岂非贵心迹之并哉 古称名士风流,必曰门庭萧寂、坐鲜杂宾,至以青蝇为吊客,岂非贵心迹之并哉?夫曰取不欲闻之语,不欲见之事,不欲与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强应酬,使吾耳目形骸为之用,而欲其性情渊夷、神明恬寂,作比兴、风雅之言,其趣不亦远乎? ……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虚心直躬,可以适己,可以行事,可以垂文。(钟惺《简远堂近诗序》)
或曰,东坡之文似战国。予曰,有东坡文而战国之文可废也。何以明之?战国之言非纵横则名法,于先王之仁义道德礼乐刑政无当焉,而其文终古不可废者,以其雄博高逸之气,纡回峭拔之情,当存于天地之间也。使战国人舍其所为纵横名法,而以为仁义道德礼乐刑政之言,则其心手不相习,志气不相随,必不能如是雄博,如是高逸,如是纡回峭拔,以成其为战国之文。故文之存,理之亡也,夫必亡理而后存文,则是理者词之祟而文之贼也。岂有是哉?今且有文于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气,纡回峭拔之情,以出入于仁义道德礼乐刑政之中,取不穷而用不敝,体屡迁而物多姿,则吾必舍战国之文从之,其惟东坡乎。(钟惺《东坡文选序》)
第六节 陈子龙与艾南英
第二章 明代的戏曲批评 明初的戏曲批评 嘉靖、隆庆时期的戏曲批评 吴江派与临川派的争论 王骥德及晚明其他戏曲批评家
第一节 明初的戏曲批评 高则成的戏曲观 朱权和《太和正音谱》 贾仲明和《录鬼簿续编》
第二节 嘉靖、隆庆时期的戏曲批评 李开先 何良俊和王世贞 徐渭和南词叙录 李贽
一、李开先 (一)真诗在民间 为诸生日,慕其名,已丑第进士,即托举主王中川致书,时崆峒已病,枕上得书叹息,以为世亦有同心如此者。(《李崆峒传》)
忧而词哀,乐而词亵,此今古同情也。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锁南枝》,一则商调,一则越调。商,伤也;越,悦也;时可考见矣。二词哗于市井,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艳亵狎,不堪入耳,其声则然矣,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虽君臣友朋,亦多有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三百篇》太半采风者归奏,予谓今古同情者此也。(《市井艳词序》)
(二)由古而俗 学诗者,初则恐其不古,久则恐其不淡;学文者,初则恐其不奇,久则恐其不平;学书、学词者,初则恐其不劲、不文,久则恐其不软、不俗。唐荆川之于诗,王南江之于文,方两江之于书,予之于词,其事异而理同,致百而虑一者乎!予词散见者勿论,已行世者,辛卯春有《赠对山》,秋有《卧病江皋》,甲辰有《南吕小令》。《登坛》及《宝剑记》,脱稿于丁未夏,皆俗以渐加,而文随俗远。至于《市井艳词》,鄙俚甚矣,而予安之,远近传之。(市井艳词又序》)
音多字少为南词,音字相半为北词,字多音少为院本;诗余简于院本;唐诗简于诗余,汉乐府视诗余则又简而质矣,《三百篇》皆中声,而无文可被管弦者也。由南词而北,由北而诗余,由诗余而唐诗,而汉乐府,而《三百篇》,古乐庶几乎可兴,故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呜呼!扩今词之真传,而复古乐之绝响,其在文明之世乎!(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 北曲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故词情多而声情少。南曲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故词情少而声情多。(王世贞、魏良辅)
二、何良俊和王世贞 何良俊 国朝科目限人,长才者或悭一第,如文征明、王宠文、彭文嘉、何良俊、田艺蘅、欧大任,文章俱足名世,独靳一举,竟以岁贡起家,岂非命耶!(明徐火勃) (一)推崇北曲
传奇戏文,虽分南北,套词小令,虽有短长,其微妙则一而已。悟入之功,存乎作者之天资学力耳。然俱以金、元为准,犹之诗以唐为极也。何也?词肇于金,而盛于元,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乐于心而声于口,长之为套,短之为令,传奇戏文,于是乎侈而可准矣。……国初如刘东生、王子一、李直夫诸名家,尚有金、元风格,乃后分而两之,用本色者为词人之词,否则为文人之词矣。(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
金、元人呼北戏为杂剧,南戏为戏文。近代人杂剧以王实甫之《西厢记》,戏文以高则诚之《琵琶记》为绝唱,大不然。夫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歌曲,则歌曲乃诗之流别。今二家之辞,即譬之李、杜,若谓李、杜之诗为不工,固不可;苟以为诗必以李、杜为极致,亦岂然哉?祖宗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辞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世人不得尽见,虽教坊有能搬演者,然古调既不谐于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听者即不喜,则习者亦渐少,而《西厢》《琵琶记》传刻偶多,世皆快睹,故其所知者,独此二家。余所藏杂剧本几三百种,旧戏本虽无刻本,然每见于词家之书,乃知今元人之词,往往有出于二家之上者。盖《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苟诗家独取李、杜,则沈宋、王、孟、韦、柳、元、白,将尽废之耶?(《曲论》)
余谓其(指《拜月亭》——引者)高出于《琵琶记》远甚。盖其才藻虽不及高,然终是当行。其“拜新月”二折,乃檃栝关汉卿杂剧语。他如走雨错认上路馆驿中相逢数折,彼此问答,皆不须宾白;而叙说情事,宛转详尽,全不费词。可谓妙绝。
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辞老健而乏滋媚,关之辞激厉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 郑德辉杂剧,《太和正音谱》所载总十八家。然入弦索者,惟《梅香》、《倩女离魂》、《王粲登楼》三本。 此九种即所谓戏文,金元人之笔也。词虽不能尽工,然皆入律。正以其声之和也。夫既谓之辞,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
一、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宛转为主,各有不同。至于北曲之弦索,南曲之鼓板,犹方圆之必资于规矩,其归重一也。故唱北曲而精于[呆骨朵]、[村里迓鼓]、[胡十八],南曲而精于[二郎神]、[香遍满]、[集贤宾]、[莺啼序];如打破两重禅关,余皆迎刃而解矣。 一、北曲与南曲,大相悬绝,有磨调、弦索调之分。北曲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故词情多而声情少。南曲家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故词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索,宜和歌,故气易粗。南力在磨调,宜独奏,故气易弱。近有弦索唱作磨调,又有南曲配入弦索,诚为方底圆盖,亦以坐中无周郎耳。(魏良辅)
(二)强调舞台性 此九种(《吕蒙正》等)即所谓戏文,金元人之笔也。词虽不能尽工,然皆入律。正以其声之和也。夫既谓之辞,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 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斟量。(沈璟《二郎神套曲》) 宁律协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沈璟)
王世贞 王世贞只写过一些散曲,少而不精,对戏曲既无创作,又无研究,写作态度也不认真。 只是由于当时曲话之作很少,而他的文名又大,《曲藻》才引起人们的重视。 ——徐朔方 就作家来说,他强调才情学问;就戏曲文体的特征来说,他以诗为曲;就戏曲文体的内部要素来说,他重视文辞甚于音律;就文辞来说,他更倾心于骈绮的风格。”(李延贺)
(一)戏曲史流变与俗化倾向 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
(二)戏曲修辞论 则成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调微有未谐,譬如见锺王迹,不得其合处,当精思以求谐,不当执末以议本也。(王世贞《曲藻》)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
马致远《百岁光阴》放逸宏丽而不离本色。押韵尤妙,长句如:“红尘不向门前惹,緑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东缺。”又如:“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俱入妙境小语。如“上床与鞋履相别”,大是名言,结尤疎俊可咏。元人称为第一,真不虚也。 (王世贞)
《琵琶记》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撰。亦佳。元朗谓胜《琵琶》,则大谬也。中间虽有一二佳曲,然无词家大学问,一短也;既无风情,又无禆风教,二短也;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堕泪,三短也。《拜月亭》之下,《荆钗》近俗而时动人,《香囊》近雅而不动人,《五伦全备》是文庄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烂。
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此吾论曲三昧语。
“杨状元慎才情盖世,所著有《洞天玄记》、《陶情乐府》、《续陶情乐府》流脍人口,而颇不为当家所许。盖杨本蜀人,故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也。”“常明卿有《楼居乐府》,虽词气豪逸,亦未当家。”“近时冯通判惟敏,独为杰出,其板眼、务头、撺抢、紧缓,无不曲尽,而才气亦足发之;止用本色过多,北音太繁,为白璧微颣耳。金陵金白屿銮,颇是当家,为北里所贵。”
三、徐渭和《南词叙录》
(一)关于南北曲 主要内容 南戏源流与发展 风格特色 声律 作家作品评论 常用术语、方言的考释 戏本目录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宋词遂绝,而南戏亦衰。顺帝朝,忽又亲南而疏北,作者蝟兴,语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也。
永嘉高经历明,避乱四明之栎社,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相传:则成坐卧一小楼,三年而后成。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尝夜坐自歌,二烛忽合而为一,交辉久之乃解。好事者以其妙感鬼神,为剙瑞光楼旌之。我高皇帝即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既而曰:“惜哉,以宫锦而制鞵也!”由是日令优人进演。寻患其不可入弦索,命教坊奉銮史忠计之。色长刘杲者,遂撰腔以献,南曲北调,可于筝琶被之;然终柔缓散戾,不若北之铿锵入耳也。
今南九宫不知出于何人,意亦国初教坊人所为,最为无稽可笑。①夫古之乐府,皆叶宫调;唐之律诗、绝句,悉可弦咏,如“渭城朝雨”演为三迭是也。至唐末,患其间有虚声难寻,遂实之以字,号长短句,如李太白《忆秦娥》、《清平乐》,白乐天《长相思》,已开其端矣;五代转繁,考之《尊前》、《花间》诸集可见;逮宋,则又引而伸之,至一腔数十百字,而古意颇微。徽宗朝,周、柳诸子,以此贯彼,号曰“侧犯”、“二犯”、“三犯”、“四犯”,转辗波荡,非复唐人之旧。晚宋,而时文、叫吼,尽入宫调,益为可厌。② “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间有一二叶音律,终不可以例其余,乌有所谓九宫?必欲穷其宫调,则当自唐、宋词中别出十二律、二十一调,方合古意。是九宫者,亦乌足以尽之?多见其无知妄作也。
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很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弦管,南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浅俗可嗤。然其间九宫、二十一调,犹唐、宋之遗也,特其止于三声,而四声亡灭耳。至南曲,又出北曲下一等,彼以宫调限之,吾不知其何取也。或以则诚“也不寻宫数调”之句为不知律,非也,此正见高公之识。夫南曲本市里之谈,即如今吴下《山歌》、北方【山坡羊】,何处求取宫调?必欲宫调,则当取宋之《绝妙词选》,逐一按出宫商,乃是高见。彼既不能,盍亦姑安于浅近。大家胡说可也,奚必南九宫为?
(二)推崇本色 南曲固是末技,然作者未易臻其妙。《琵琶》尚矣,其次则《翫江楼》、《江流儿》、《莺燕争春》、《荆钗》、《拜月》数种,稍有可观,其余皆俚俗语也;然有一高处:句句是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 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况此等耶?直以才情欠少,未免辏补成篇。吾意: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也?
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者煦煦也。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西厢序》,《徐文长佚草》卷一)
《晋书·天文志中》,“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顺时应节……不失本色而应其四时者,吉。”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 严羽:“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陈师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
句法中有字面,若遇中有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 (顾瑛) (1)曲词修辞的本色 盖《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何良俊) (《拜月亭》)“其[拜新月]二折,乃隐括关汉卿杂剧语。他如‘走雨’、‘错认’、‘上路’、馆驿中相逢数折,彼此问答,皆不须宾白,而叙说情事,宛转详尽,全不费词,可谓妙绝。” (何良俊)
元曲为曲之一变,……若其体则全与诗词作品别,取直而不曲,取俚而不取文,取显而不取稳,盖此乃述古人之言语,使愚夫愚妇共见共闻,非文人学士自吟自咏之作也。若必铺叙故事,点染词华,何不竟作诗文,而立此体耶?譬之朝服游山,艳妆玩月,不但不雅,反伤俗矣。但直必有至味,俚必有实情,显必有深义,随听者之智愚高下,而各与其所能知,斯为至境。又必观其所演何事,如演朝廷文墨之辈,则词语仍不妨稍近藻绘,乃不失口气;若演街巷村野之事,则铺述竟作方言可也。总之,因人而施,口吻极似,正所谓本色之至也。此元人作曲之家门也。知此,则元曲用笔之法晓然矣。 (清徐大椿)
四、李贽
第三节 吴江派与临川派的论争 论争的概况 沈璟和吴江派 臧懋循 吕天成 冯梦龙 汤显祖 王思任、孟称舜和茅元仪
一、论争概况
于万历三十五年或略后,孙如法以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寄汤显祖,汤显祖作书以答之。书中有“此亦安知曲意哉”、“弟在此自谓知曲意者,笔懒韵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等语。
茅暎说:(音律与辞藻)“二者固合则并美,离则两伤”。 吕天成说:“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
二、沈璟的戏曲史命题 易弦索而箫管,陶激烈于和柔。令听者解烦释滞,油然觉化日之悠长。( 冯梦龙《太霞新奏序》)
[二郎神]何元朗,一言儿启词宗宝藏。道欲度新声休走样,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斟量。
三、汤显祖的文化命题 ……曲谱诸刻,其论良快。久玩之,要非大了者。《庄子》云:“彼乌知礼意。”此亦安知曲意哉。其辨各曲落韵处,粗亦易了。周伯琦作《中原韵》,而伯琦于伯辉致远中无词名。沈伯时指乐府迷,而伯时于花庵、玉林间非词手。词之为词,九调四声而已哉!且所引腔证,不云未知出何调犯何调,则云又一体又一体。彼所引曲未满十,然已如是复何能纵观而定其字句音韵耶?弟在此自谓知曲意者,笔懒韵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答孙俟居》)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冥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牡丹亭题词》)
四、汤沈之争的影响 臧懋循论作曲之“三难”:
何元朗评施君美《幽闺》远出《琵琶》上,而王元美目为好奇之过。夫《幽闺》大半已杂赝本,不知元朗能辨此否?元美千秋士也,予尝于酒次论及《琵琶》梁州序、念奴娇序二曲,不类永嘉口吻,当是后人窜入,元美尚津津称许不置,又恶知所谓《幽闺》者哉?予家藏杂剧多秘本,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因为参伍校订,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厘成十集,藏之名山而传之通邑大都,必有赏音如元朗氏者。(《元曲选序》)
自词隐作词谱,而海内斐然向风。衣钵相承,尺尺寸寸守其矩矱者二人:曰吾越郁蓝生,曰檇李大荒逋客。郁蓝《神剑》、《二媱》等记,并其科段转折似之;而大荒《乞麾》至终帙不用上去叠字,然其境益苦而不甘矣。 (王骥德) 大荒奉词隐先生衣钵甚谨,往往绌词就律,故每多生涩之病。 (冯梦龙)
词学三法:曰调、曰韵、曰词。不协调则歌必捩嗓,虽烂然词藻,无为矣。自东嘉沿诗余之滥觞,而效颦者遂籍口不韵。不知东嘉宽于南,未尝不严于北。谓北词必韵而南词不必韵,即东嘉亦不能自为解也。是选以调协韵严为主。二法既备,然后责其词之新丽。若其芜秽庸淡,则又不得以调韵滥竽。 (冯梦龙《太霞新奏发凡》) 余词不敢较玉茗,而差胜之二:玉茗不能度曲,予薄能之。虽按拍不甚匀合,然凡棘喉殢齿之音,早于填时推敲小当,故易歌演也。(阮大铖)
第四节 王骥德和晚明其他戏曲批评家 王骥德 徐复祚 凌濛初 祁彪佳
王骥德的曲学体系 (《曲律》)即成,功令条教,胪列具备,真可谓起八代之衰,厥功伟矣!(吕天成《曲品自序》) 明代之论曲者,至于伯良,如秉炬以入深谷,无幽不显矣。(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无骥德则谱律之精微、品藻之宏达,皆无以见,即谓今日无曲学可也。(任中敏《曲谐》)
起首两章具有绪论性质。《论曲源》阐述“曲”的渊源及其流变大略;《总论南北曲》比较南、北曲的风格特征并概言其形成历史。以下各章则或专论南曲,或以论南曲为主。 第三至第三十八章为分论部分,可分为“声律”、修辞“、”曲词“、”剧戏“四方面。 ■声律论包括第3至第12的十章,是关于音韵与声乐的理论。 ▲《论调名》介绍曲牌名的来历、构成方式,并附录沈璟《南九宫谱》、蒋孝《十三调南曲音节谱》诸曲名目以及王氏新制曲调名目。 ▲《论宫调》择要复述前人有关宫调问题的论述,概述对宫调的认识与应用的衍变沿革。 ▲《论平仄》简说唱曲与平仄四声的关系,指出“至调其清浊,叶其高下,使律吕相宣,金石错应,此握管者之责,故作词第一吃紧义也。” 《论阴阳》阐明字分阴阳在南曲中的应用意义,并举例说明作曲时如何使阴、阳字与曲调旋律取得和谐 的配合。 《论韵》提出南、北曲用韵必须有所区别,反对传奇创作用韵一依《中原音韵》成法。 《论闭口》字主张保留闭口字的读音,反对开口、闭口字同押。 《论务头》对前人有关“务头”的一些说法略加考辨,并提出通过“反复歌唱,谛其曲折”来取“务头”所在的新解。 《论腔调》介绍传统的唱曲理论,并重点考察南曲声腔的流变及昆山腔的地方流派。 《论板眼》略述有关板眼的一般常识。 论须识字》举例说明误读字音、误用字韵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通病,从而提醒说“作曲与唱曲者,可不以考文为首务耶”。
第三章 明代的小说批评 第一节 历史小说论 第二节 吴承恩及谢肇淛 第三节 李贽与叶昼 第四节 有关《金瓶梅》的批评 第五节 冯梦龙及其他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冯梦龙《警世通言·叙》) 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
一、明清时期的演义观 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 俗不可通,则义不必演矣。……予为通俗演义者,非敢传远示后,补史所未尽也。(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 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鄙可嗤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下) 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演义者,小说之别名。(刘廷玑《在园杂志》)
(一)把“历史演义”视为正史的通俗版,正史的普及读物。把“历史演义”定位在正史与野史之间。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帮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 然史之文,理微义奥,不如此,乌可以昭后世?《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罗贯中编《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盖欲与《三国志》并传于世,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予既不计年劳,抄录成帙,……后之君子能体予此意,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盖予之至愿也夫。(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
客问于余曰:刘先主、曹操、孙权,各据汉地为三国,史已志其颠末,传世久矣,复有所谓《三国志通俗演义》者,不几近于赘乎? 余曰:否,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檃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好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故继诸史而作《列国传》,起自武王伐纣,迄于秦并六国;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凡英君良将,七雄五霸,平生履历,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而逐类分沉。且又惧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辞奥旨,复又改为演义,以便人观览,庶几后生小子开卷批阅,虽千百年往事,莫不炳若丹青,善则知劝,恶则知戒,其视徒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者,信天渊相隔矣。继群史之遐纵者,舍兹传其谁归?(余邵鱼)
(二)把“历史演义”当成野史。 《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高儒)
(三)把“历史演义”当成小说。 (1)既是小说,则遵循小说想象的规律
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之以备参考。 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其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如西子事,昔人文辞往往及之,而其说不一。《吴越春秋》云吴亡西子被杀,则西子在当时固已死矣。唐宋之问诗云:“一朝还旧都,靘妆寻若耶。鸟惊入松网,鱼畏沉荷花。”则西子尝复还会稽矣。杜牧之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是西子甘心于随蠡矣。及东坡《题范蠡》诗云:“谁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则又以为蠡窃西子,而随蠡者或非其本心也。质是而论之,则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矣。(熊大木)
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浒传》无论已,《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其他诸传记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国演义》与《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矣。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 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影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
《列国志》与别本小说不同,别本都是假话,如《封神》、《水浒》、《西游》等书,全是劈空撰出,即如《三国志》,最为近实,亦复有许多做造在内。《列国志》却不然,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实事也记不了,那里还有功夫云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蔡元放)
第二节 吴承恩与明代的小说奇幻论 (第二节 吴承恩及谢肇淛) 第二节 吴承恩与明代的小说奇幻论 (第二节 吴承恩及谢肇淛)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一,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 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 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干宝)
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张籍) 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为中不失正,将以苟悦于众,是戏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义之道也。(张籍) 驳杂之讥,前书尽之,吾子其复之,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也。(韩愈) 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裎也。(韩愈)
否,否,不然. 子以为子之史皆信邪. 子之子皆伦邪. 子之子、史皆中道邪. 一有非信非伦,则子、史之诬均;均诬则去此书非远,余何从而定之 否,否,不然!子以为子之史皆信邪?子之子皆伦邪?子之子、史皆中道邪?一有非信非伦,则子、史之诬均;均诬则去此书非远,余何从而定之?故以大道观,皆非所宜有矣。以天地之大观,何所不有哉……是故必兼存之后可,于是兼存焉。(陈元之《刊西游记序》)
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 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俶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涯涘,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已。(陈元之《刊西游记序》)
说到装天处,令人绝倒。何物文人,奇幻至此。大抵文人之笔,无所不至,然到装天葫芦,亦观止矣。”(第33回总批) 这回想头,奇县,幻甚。真是文人之笔,九天九地,无所不至。”(第53回写唐僧、猪八戒子母河受孕,其总批) 唐僧化虎,白马变龙,都是文思极灵极妙、文笔极奇极幻处。作举子业的秀才如何有此!(第30回总批)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
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至于文章之妙,《西游》、《水浒》实并驰中原。今日雕空凿影,画脂镂冰,呕心沥血,断数茎髭而不得惊人只字者,何如此书驾虚游刃,洋洋洒洒数百万言,而不复一境,不离本宗。日见闻之,厌饫不起,日诵读之,颖悟自开也!故闲居之士,不可一日无此书。(慢亭过客)
史以遗名者何. 所以辅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 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 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 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奇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咯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忧惚不可方物。(袁于令《隋史遗文序》)
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资齿牙,不可动肝肺。《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矣。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间乎?尝譬诸传奇,《水浒》,《西厢》也;《三国志》,《琵琶记》也;《西游》则近日《牡丹亭》之类矣。他如《玉娇梨》、《金瓶梅》,另辟幽蹊,曲终奏雅,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谓奇书,无当巨览,其《水浒》之亚乎。他如《七国》、《两汉》、《两唐宋》,如弋阳劣戏,一味锣鼓了事;效《三国志》而卑者也。《西洋记》如王巷金家神说谎乞布施,效《西游》而愚者也;至于《续三国志》、《封神演义》等,如病人呓语,一味胡谈。《浪史》、《野史》等,如老淫土娼,见之欲呕,又出诸杂刻之下矣。(三遂平妖传》)始终结构,有原有委,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张无咎)
《水浒》 ——《玉娇梨》《金瓶梅》 《三遂平妖传》 《西游》——《西洋记》 《三国志》—— 《七国》、《两汉》、《两唐宋》 《续三国志》《封神演义》——如病人呓语,一味胡谈 《浪史》《野史》——如老淫土娼,见之欲呕
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昔华人到异域,异域咤以牛粪金。随诘华人之异者,则曰有虫蠕蠕,而吐为彩缯绵绮,则可以衣被天下。彼舌挢而不信。乃华人未之或奇了。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赘矣。(即空观主人)
第三节 李贽与叶昼
1. 容与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 2. 袁无涯刊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 (万历三十八年)[出自叶昼手笔] (差不多同时)[部分出自袁无涯、冯梦龙手笔]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
第四节 有关《金瓶梅的批评》
第五节 冯梦龙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