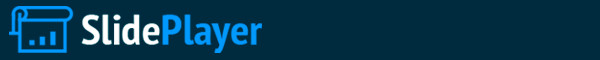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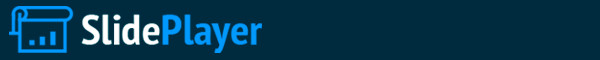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認知的先天局限(上) 文字取材: 霍韜晦
人與存在分離 學東方的文化最重要是體證,人生成長須經此關,學佛學更要身經此關。如果不懂得體證,根本不能進入學佛之門。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體證不是空說概念、符號或語言,而是超越語言、文字、符號的阻隔,所以是極難的。《維摩經》中記載維摩居士以「默然無言」來展示如何得入「不二法門」。「不二法門」是最高之法門,是對最高存在之體證。一般人把「不二法門」理解為唯一的方法,這是依字面解,這當然不是《維摩經》之解釋,也不是佛教之意思。
根據佛教之哲學,「不二」首先是討論存在;佛教所關注的問題是「人」和「存在」如何重新結合為一體。蓋人自有意識活動便與存在分離,以基督教之語言來說是人與上帝分離,所以基督教把人的問題、人的方向、人的命運回歸於神來解決。 「Religion」之意思便是回歸,重新去認知、體會神,與神重新結合。所以宗教是「Union with God」,或「Re-union with God」。但佛教的問題是人與存在分離,人不認識自己,不認識生命,不認識世界,不認識真實,這才是佛教所提出的問題。「真實」是什麼?人人皆以為得著真理,以為自己能得到對世界、對人的解釋,包括對自己的解釋,但結果所得的只是虛妄而不是真實。理由在那裡呢?
主觀經驗不能證入真實 在這裡首先要碰上的是知識問題。 人對世界的理解首先必須通過經驗,通過「眼、耳、鼻、舌、身」等感官之活動,觀察所得,然後提供給意識思維。人對世界之思維不能沒有材料,不能沒有經驗,所以「色、聲、香、味、觸」便是佛教所總結出的人的原始經驗、感性經驗,從這立場看佛教與西方的經驗主義沒有太大之分別,西方哲學家談知識問題,也是從感性經驗開始。
我們用眼所看到的是種種的顏色形狀;我們用耳朵所聽到的種種聲音。總之,人與外界溝通的渠道是眼、耳、鼻、舌、身,透過這些渠道,外界的色、聲、香、味、觸便得以進入。但如果我們所得到的這些原始經驗,便等如真正的外在世界,豈不是人人都自以為得到真實?那又怎會有「瞎子摸象」的故事呢?四個瞎子皆用手去摸象,但結果沒有人能得到象之全相,所得到的只是象的片面 -------鼻子、耳朵、大腿、尾巴。
這便是瞎子摸象之經驗,以主觀所得來代替客觀世界,由相信自己之眼睛與思維,結果提出了自己之世界觀,進一步更以為這是唯一的真實,並排斥別人的見解,於是成為最樸素之經驗主義者與唯我論者,如古希臘之「智者」,以為人是萬物之量尺( Men in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 一切以自己的經驗為依歸,這無疑是幼稚之觀點,但居然為一般人所接受。所以從樸素的經驗主義會走向相對主義和極端唯我主義,世界只是我的世界,知識都只是我的知識,別人的觀點與我不相干,也不可能有意義。
唯我論所代表的絕對封閉的系統,同時由於對別人的世界完全予以排斥,結果客觀存在無從建立,知識的標準無根,這便成為懷疑論,如英國的巴克萊和休謨。所以,一定要從自我的封閉系統中超越出來。但「超越」自己是一個很難之課題,如何超越自己呢?難道要不信自己的眼?不信自己的心?知識若起源於經驗,則一切判斷也靠個人的經驗支持,但人與人之間的經驗不能易處,這便是鴻溝,所以,到最後必然是各人自說自話,等如莊子與惠施之辯論一樣:二人游於濠梁之上,莊子道:游魚真是逍遙快樂,惠施卻反駁他說:「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然後莊子又反駁他說:「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結果就是永遠也不能得到結論。
知識的客觀性與局限性 以上我們談的是知識問題:知識的客觀性如何建立?可以說是非常之難。知識的客觀性在西方哲學史上引起了巨大的思考。經驗主義者認為人自身的經驗才是準則;理性主義則認為人的思維法度才是準則;實在論者、唯物論者以符合客觀存在為界線,但自休謨的懷疑論出,破除存在本體,結果把懷疑主義帶進虛無主義,知識完全沒有客觀根據。
另一邊廂,理性論者卻堅持要把知識的客觀性建立起來,所以以極力要提出一套規律,這便是理性標準,包括因果、必然、目的,希望通過這些目的、因果、必然等概念之使用,找到一個共同秩序,以此來建立客觀規範。但這些客觀規範到了最後是否保得住?如所謂因果,它是我們思維的規律(格式)?還是在自然世界中自存?現象世界的變化是否遵守因果規律?它是機械的?還是隨人的意志而轉移的?
一般來說,理性主義相信因果有必然性,但休謨卻從經驗立場加以攻擊。他認為我們所經驗到的只是個別的現象,如吸煙與癌症,這兩個現象之間有何關係?此關係我們不能經驗。照休謨說,這些看似有因果相連的現象,只是不斷重複的經驗的再現,其間只能說是習慣所成。如天昏便下雨,我們多次經驗到兩者在時間上之連續,而形成心理習慣:每次見到天昏,便預期快將會下雨。其實,這是經驗習慣,誰人能保證兩者有必然關係呢?吸煙和癌症的關係亦然。
所以在這裡,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引起了很大的爭論。理性主義者認為有因果,但經驗主義者卻反詰如何證明有因果,到康德時方有兩者之綜合:把因果列屬於理解世界時的先驗格式,感性提供經驗素材,正如我們在工廠處理原料時必須要有一個模型。模型便是形式,原料只是素材,原料與模型結合才能產生產品。知識也是產品,當人處理經驗素材時,必須要有一方式,而這方式是先在的,所以不用學,例如因果、數量、質量等,都是思維世界的法則,當我們運用思考力去思考世界時,必須通過這些範疇,正如用模型來處理原料一樣。
原料是甚麼呢?原料便是我們的原始經驗,是我們用眼、耳、鼻、舌、身捕捉回來之素料,兩家結合方才產生知識。由於有原料之限制,所以康德說,知識只能從現象界說,而不能對本體說。因為對本體,我們不能有經驗。如上帝,我們能否知道上帝是甚麼顏色呢?是否知道上帝發出了甚麼聲音呢?能否知道上帝有多高呢?皆不能,所以,我們不能對上帝有任何資料、有任何經驗,又或者對靈魂的問題,我們亦沒有任何經驗。
同一道理,我們一直認為,經驗來源於客體自身,我們對之亦不可以有任何知識。譬如對一隻水杯,我們所能得到的是它的色澤、形狀、軟硬,但杯的自身,我們是不可得知的,我們所能捕捉的只是杯之屬性(attributes),而不是杯之自身(itself),或者德文稱之為“noumena”,就是所謂「物自身」或「本體」。「本體」是我們用來理解事物存在之假設性慨念,用來解釋對象的獨立性,否則我們對對象的知識無處落腳。
但「本體」是我們無法認知的,因為我們對「本體」沒有任何經驗,所以康德認為知識只能到達現象界而不能指涉「本體界」,「物之自身」不可知。但這樣,知識便只有經驗這一層,而且受感性局限,受認知主髒局限,始終不能去除主觀性和相對性;亦即不能達到「物自身」,則一切認知,都只能內在於認知主體的活動中說。
這一個問題如果從科學立場看,可更明白:依科學立場,由於方法論的性質,科學知識無絕對,永遠在待檢證和待否證的狀態中。科學知識只是邁向真理,但它不是最後的真理,換言之,一切科學知識都尚有虛妄的可能,理由就是我們永遠從有限的定點觀察現象,而現象的本質則永遠在我視野之外。
人為甚麼要付代價? 若能明白此義,則佛教所說的「如實觀」便很重要。佛教要我們了解真實的世界,這樣才不會有虛妄的情形出現。依據佛教的前提:人若陷於虛妄,便會產生錯誤知識,由錯誤的知識,便會引生錯誤的行為,這就是「業」,由「業」而有「報」。
為甚麼有報呢?乃是由於行為出現了偏差;行為為甚麼會有偏差呢?皆因對客觀世界的了解不如實,不知其存在的方式與秘密,一味錯認。用佛教的話來說,也就是不見法、不見理,所以行為亦不如法、不如理。依此,人生便要付出代價。在這裡,我們可看出佛教思想的前提:如法、如理的行為沒有業、沒有報,只有不如法、不如理的行為要償付代價;如是因,即有如是果。這就是人生活動的公平原則。
所以佛陀並非不作事、不說話,而是佛陀之言行全然合理、合法,因此沒有要償付的東西。佛陀常被稱為「如來」,「來」指他的活動、行為。佛陀之一言一行、一舉手、一投足皆合乎存在之法則,使其生命達於圓滿的地步,故佛陀為圓滿人格。佛陀的活動為甚麼能夠「如來」?就是因為他有如實觀,能夠把握存在之真實,包括生命的真實。
如實觀是關鍵,一般人不能有如實觀,正如西方經驗主義者所言,我們是用眼來看世界,用意識來思維世界,結果被其經驗局限。依我們上文分析,不但經驗主義者有其局限,即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同樣有其局限。為甚麼?就是因為他們用以探討存在的工具是感性與理性,都是從一個有限的定點來看問題,結果都無法跨越其自身之障礙。
這一障礙,佛教便稱之為「無明」,「無明」者沒有光,見不真切,錯認世界、錯認人生。這種錯認,造成對自己的封閉。人在這一封閉圈內活動,就是盲目亂動,所以須付代價。從另一角度看,也就是把自己和真實的存在隔絕開來,無法徹入存在世界的秘密,也就是不能得「法」。
「法」是秩序,也是道理。但「無明」把人和道理阻隔起來,這就是人的現實、人的罪、人的苦。存在的理法不是人製定的,也不是上帝所立,而是本來如此。它內在於世界,內在於存有。存在與理法本來合一,生命與存在亦合一。現象界的規律並非真正的規律,只是我們的觀察所得。真正的「法」是無人間符號的,只能徹入。花謝花開,流水白雲,畢竟誰為因?誰為果?生老病死亦然。
如果以為現象的次第呈現就是因果,如休謨所說,則何有因果?只能默然。偏偏人要依照自己之觀察去解釋世界,找尋因果,科學便是走這一條路 - 觀察世界,提出設準,然後驗證(verification)。經多次驗證,而且沒有反例,便成為科學知識。科學知識的支持在歸納,但歸納永無窮盡,凡涉及經驗者都無必然,所以不能得出普通命題。
近代的卡納普(R.Carnap)便索性以慨率邏輯來代替歸納法,承認科學知識只是一或然真理,所以Karl Popper主張:科學知識可以改寫;牛頓之力學、物理學會被愛恩斯坦改寫,道理便是如此。科學知識是不斷進步、不斷被修改、沒有絕對性、是在不斷邁向真理之過程中,在科學世界不能說有永恆絕對之真理。這是依其知識建立的方法和本質上說。
科學知識不能安身立命 由於科學知識的局限,所以科學知識不能安身立命。如真的有人透過科學知識而賴以安身立命,則他也不是依賴科學知識本身,而是依賴對科學之信仰,以科學取代上帝,因此可以說是科學主義者。就科學知識而言,其恆真性與穩定性是不足的。西方的進路,將自然世界,甚至將生命自身,均視作認知之對象,加以觀察,則生命、世界最後存在之本相是不能獲得的,這是因為其方法論的局限性。
科學知識只能視作我們對客觀真理探求的過程,而不能視作最後之標準。科學知識是人和世界的中介,正如現在我們探求火星現象,只能透過衛星拍攝所得之照片來研究,但照片畢竟不是火星。照片終歸是中介,未能完全表現客體,一旦攝影技術再進一步,便完全是兩回事。等如物理學,觀察工具越精細,知識愈有機會突破,所以方法論是關鍵。
科學方法必須將世界當作對象來觀察,這是二分法。不但物理現象,就算討論人生、討論社會,也用上這種二分法來處理。如生理學、生物學研究人體,便在手術台上作剖析觀察,又或者透過影像、掃描機來拍攝,「我」永遠是抽離之研究者。這種人與知識之二分,造成人與知識的對立,中有鴻溝,永遠不能越過。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