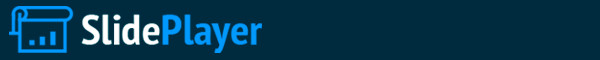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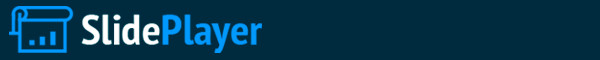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明代的诗文批评
高棅《唐诗品汇》 元代杨士宏《唐音》十四卷,分为始音、正音、遗响。 唐棅称赞其“能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可谓能得唐人三尺矣。” 1、别体制之始终。“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堕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 “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傍流。” 2、由音声以辩诗。五言古诗:正宗——陈子昂、李白;大家——杜甫;名家——孟浩然、王维、王昌龄等;七言古诗:正宗——李白;大家——杜甫;名家——高适、岑参等;七言绝句:正宗——李白、王昌龄;正变——李商隐、杜牧等;五言律诗:正宗——李白、孟浩然、王维、岑参、高适;大家——杜甫;
李东阳茶陵诗派 《麓堂诗话》:1、首重诗文之别。诗之体与文异……盖其所谓有异于文者,以其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覆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取类于鸟兽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 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诗又其成声者也。若歌吟咏叹,流通动荡之用,则存乎声,而高下长短之节,亦截乎不可乱。 2、初步提出“格调”说。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体格),耳主声(声调)。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辩五色线,此具眼也。费侍郎廷言尝问作诗,予曰: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乃为有得。 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翰林院任职29年、参与内阁机务18年,领袖文坛,一时诗人奉以为宗,称茶陵诗派。李东阳合声调格律以论诗,这便是他得格调说。其特点是在理论上从诗与乐的关系出发,以声调来辨析诗体;而在实际的批评中,又时时从句法、字法等诗律问题着眼,研析入微。
《潜虬山人记》: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 弘治、正德:李梦阳、何景明 《明史·文苑传序》:“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 1、学不的古,苦心无益。晚年《与周子书》:“仆少壮时振翮云路,尝周旋鵷鸾之末,谓学不的古,苦心无益,又谓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当是时笃行之士,翕然臻向。弘治之间,古学遂兴。”(徐祯卿、康海、边贡、王廷相、王九思) 《潜虬山人记》: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 第二,他们标榜复古是与求真的意图密切相关的。
第一,从他们所标举的古代作家作品来看,他们并非一味地只从形式方面去倡言复古。如他评论曹植“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阮籍“洋洋乎会于风雅”,陶渊明“俯仰悲慨,玩世肆志只心焉”。何景明论诗既重辞,亦重意,说:“辞意并亡,而斯道废矣。”(《海叟集序》,) 第二,他们标榜复古是与求真的意图密切相关的。李梦阳《诗集自序》记载王叔武“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真诗乃在民间”的说法,为之感动。李梦阳“废唐近体诸篇而为李杜歌行”,并由此上溯,为六朝、晋魏、两汉、诗三百,体现出追本求源的思想。在学古时要求得第一义,而所谓第一义是指各类诗歌题材初兴时期最富有生命力的作品,风格浑朴,与民歌较为接近。故提倡“第一义”和追本寻源、重视民歌的观点,都是追求真情实感得流露,反对虚假地矫揉造作。这是李梦阳所倡导地文学复古运动地精神所在。当然复古与求真之间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2、格古调逸,情以发之。李《潜虬山人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以情为本的格调说。《张公诗序》:“夫诗发之情乎?声气其区乎?正变其时乎?”《鸣春集序》:“窍遇则声,情遇则吟。吟以和宣,宣以乱畅,畅而永之,而诗生焉。”《梅月先生诗序》:“情者动乎遇者也。……故遇者物也,动者情也。……遇者因乎情,诗者形乎遇。”(感情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3、重视比兴之义。李梦阳《秦君饯送诗序》:“盖诗者感物造端者也,故曰言不直遂,比兴以彰。假物讽喻,诗之上者也,故古人之欲感人也,举之以似,不直说也,托之以物,无遂辞也,然皆始造于诗,故曰诗者感物造端者也。
李梦阳《诗集自序》:“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谔也,呻也,吟也,行(口占)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唐宋派: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 都受李、何的影响。王慎中后受王学影响,为学重视内心的体会,本性的探求,以之论文,自然不满于七子派所标榜的古文辞及格调之说,他论文以意为本,重视一己内心的体会。王说“所谓古文词者,非取其文词不类于时,其道乃古之道也。”(《与林观颐》)这是唐宋派的基本观点,称扬曾巩之文。王《与江午坡》:“其作为文字法度规矩,一不敢背于古人,而卒归于自为其言。” 唐顺之论法;唐顺之论本色。《答茅鹿门知县第二书》:“文莫犹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论,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千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
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 且夫两汉而下,文之不如古者,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不尽如哉!秦汉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家本色,纵横家有纵横家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 唐顺之的本色论是唐宋派文论得精彩之处,它尚真,它重视独特卓绝的见解,这对矫正当时七子派的拟袭、道学家的庸腐,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唐顺之后期一味的“套虚息影”、“不欲不为”,要“忍嗜欲以培天根”,故他所提倡的“本色”便显得空洞。他所作诗似寒山子、《击壤歌》。 归有光:《与沈敬甫书》:“文字又不是无本源,胸中尽有,不待安排。”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
嘉靖、隆庆:李攀龙、王世贞、谢榛 李曾“高自夸许,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也”(《列朝诗集小传》)王自称认识李后,“自是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矣”(《艺苑卮言》) 李攀龙有严重的拟古倾向,《古诗后十九首》,《古乐府》。“拟议以成变化”。王世贞说其乐府诗“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 谢榛《诗家直说》(《四溟诗话》)。 王世贞:嘉靖后期至万历初期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1、批评李何为古歌诗,亦步亦趋,不知变化,成了前人的影子,对李何流弊有较为清醒的认识。2、前期批评唐宋派,后期对唐宋派的态度有所变化,对唐宋诗文大家都有称道,并且认为宋人“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为吾用”。 “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 1、才思产生格调,2、格调是才思的境界。诗文的格调是作者个人才思的体现,反过来格调又对作者的才思起一定的制约与规范的作用。
一、王学与明代文学批评。 心学对文学批评的影响,重一己而轻外物,重冥会而轻实证,重以内心的返照为求得真知得主要途径。1、经世致用精神的消歇与诗文理论直指人心的新趋向。明代初期论文的重要人物为宋濂与刘基。宋濂主张为文要“明道”、“立教”、“辅俗化民”(《文说赠王生黼》);刘基主张“世有治乱,声有哀乐”,写作诗歌应有“美刺讽谏”的作用。这是汉唐以来儒家文论传统精神。但是宋濂与刘基的理论在明代没有得到继续衍生下去,(晚明陈子龙“忧时托志”的主张)。这一方面与明代政治、士风有关系。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说:“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李贽解释说:“一杀孝孺,则后来读书者遂无种也。无种则忠义人材岂复更生乎。”所谓读书种子断绝,实际上士对忠义操守的放弃,是明代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昙花一现后破灭的标志。明代宦官专权,士人迫于权势的压力,弃道从势,处于尴尬与绝望之中。王佑/王振,“王侍郎何无须”“老爷所无,儿安敢有?”
另一方面,与心学的兴起有关系。心学反对理学八股的积弊,以及世道人心的腐坏,主张直指本心,探索内心道德的真谛。实际上可以看作在当时的险恶政治环境中、在道学腐化的文化环境中,士人寻求驰骋心理自由的空间,在心灵主体拓展的一片新天地,是解决士人群体人生困境的方案。薛瑄(前期、理学大儒、心学先驱)晚年作诗说:“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他论学重一己之体验,故说工夫在“夙夜饮食男女衣服”等万物之间,本此论文,则(1)、饮食男女无不可道,诗文题材十分广泛。(2)、不作道学语,而要发之自然,抒写心中所不得不言者。这些观念与宋、刘大相径庭,却是永乐以后、正德之前的代表性文学主张。
陈献章(白沙):“学必有源,静而反观乎此心之体,得其自然而不假人力。”以为天下之道原自吾本心而足也。社会/自我,依傍宋儒/追求自得,学习经典/静中自悟。“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夫人所以学者,欲闻道也。苟欲闻道也,求之书籍而道存焉,则求之书籍可也;求之书籍而弗得,反而求之吾心而道存焉,则求之吾心可也。” 《明史·儒林传》: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
王守仁,王阳明所言心即理(我即理),将价值评判的权力归于自我,极大地突出了主体的地位,从而使士人的人格得以从外在的权威中摆脱出来而独立。就王阳明自己来说,是从忧谗畏讥的悲愤凄凉转向从容自得。在面对生命绝境时,发现自我良知对于生命存在的重要。“渐觉形骸逃物外,未妨游乐在天涯。”“知行合一”、“致良致”不是朱子的“格物致知”,而是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求乐、自得。
在“心物关系”上,王阳明重视的是“心”,是主体,宋人在心之上,还有一个“天理”,主张治心养气,妙合天理。王阳明思想中的心,是本善的,本来就蕴涵天理,是心赋予外物以意义。《传习录》:“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海德格尔,世界因我而存在,照亮、敞开。)
“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万物了。”人的灵明成了一切的主宰,而物则退居于次要的地位。王艮(泰州学派),狂傲之风,市民化倾向。
李梦阳的复古思潮略早于王阳明的良知之学。王阳明曾受复古思想的影响,后更弦改张,转向自己的内心,提出良知。阳明心学的出现,是主观对客观的吞没,是内容对形式的颠覆,而从文学发生上来说,则是性灵说对感物说的取代。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1、“本色论”。 嘉靖间崛起的唐宋派文人如王慎中、唐顺之等,与王阳明的思想轨迹相似,初受复古思想的影响,后接受王学,思想发生变化,才改而倡唐宋诗文。王慎中曾在南京听王畿讲解王守仁遗说,遂多有启悟,重视内心的体会、本性的探求。唐顺之提出“本色”论,(1)要求为文当有“真精神”,也即“千古不可磨灭之见”。(2)当“直抒胸臆,信手写出”。他说“真精神”“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千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其实就是王守仁所倡“虚灵明觉之良知”。唐宋大家“文以明道”“辅时及物”、“不平则鸣”等注重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与唐宋派的“洗涤心源”、“反躬为己”的观点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徐渭《西厢序》:“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即书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
2、性灵说、童心说与心学的关系。性灵一词,出现于六朝,如颜之推《颜氏家训》中就有“性灵”一词。杜甫诗歌说:“陶冶性灵成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思潮,明代诗文批评中的性灵说萌生于隆庆、万历之际。李贽《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王阳明:“勿忧文辞之不富,惟虑此心之未纯。” 李贽《读律肤说》:“盖声色之来,发于性情,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性情,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性情止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性情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 公安派袁宏道《叙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屠龙说:“夫文者,华也。有根焉,则性灵是也。”焦竑:“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
3、心学与晚明的尊情论。 明代情感论的兴盛的原因:1、是理学专制的反动。2、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扩大。3、心学、特别是王学左派的启发。 李梦阳的真情说,首次把情提到决定性的高度。王世贞提出“有真我而后有真诗”,强调情感的个性因素。
袁宏道的性灵说也提倡真情,他的真情,要求表现个性,另具有露、俗、趣的特点。“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与丘长孺》)汤显祖文学思想的核心就是“言情说”(罗汝芳):“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淡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耳伯麻姑游诗序》)又《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盖自凤凰鸟兽以至巴渝夷鬼,无不能舞能歌,以灵机自相转活,而况吾人。奇哉清源师,演古先神圣八能千唱之节,而为此道。 冯梦龙言情,万历时期主要以“冶情”或曰男女之情为内涵;后期是天启以后,其情主要以不容己之生机为内涵。
冯梦龙论《桂枝儿》《山歌》说:“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桂枝儿》等。” 《情史序·情偈》: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情。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设。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倒却情种子,天地亦混沌。无奈我情多,无奈人情少。愿得有情人,一起来演法。
公安派 公安派的理论先驱为李贽。李贽提出“童心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1、绝假纯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2、最初一念。“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好货,好色”。 袁宏道:1、古今之辩。《与江进之》:“古之不能为今者也,势也。……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古不可优,后不可劣。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 《与丘长孺》:“夫诗之气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诗之奇、之妙、之工,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各有胜处,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袭者乎?但是,他又从尚变的角度肯定时文。
2、真赝之辩。《叙小修诗》肯定《擘破玉》、《打草竿》之类民歌,“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物之传者必以质,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 3、性灵说:江盈科为袁宏道《敝箧集》作叙,引袁说:“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耳。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心能摄境,即蝼蚁蜂(万虫)皆足寄兴,不必《雎鸠》、《驺虞》矣;腕能运心,即谐词谑语皆是观感,不必法言庄什矣。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是之谓真诗,而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之为沾沾!”以性灵为诗,本质就是真,摆脱一切束缚,一任天机活波的性灵恣意翱翔。与传统的诗本性情说不同:1、露。“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2、“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3、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渐老渐失)
公安派的自我修正 公安派独抒性灵,不避俚俗,是为了矫正格调派拟古丧我之弊,但是公安派的俗俚粗率,同样是另一种新毛病。所以江盈科的诗在当时就引起人们的诘难。袁宏道43岁早逝,因此,公安派自我修正的任务,就落在袁中道(小修)肩上。袁中道对格调派与公安派之间的递转关系有较为客观的认识。《答须水部日华》: 不肖谬谓本朝修词,历下诸公,力救后来凡近之习,故于诗字字取则盛唐,然愈严愈隘,迫胁情境,使不得畅,穷而必变,亦其势然。先兄中郎矫之,多抒其意中之所欲言,而刊去套语,间入俚易。
袁宗道、宏道因为反对格调派的拘守盛唐,于是倡言宗尚白、苏。袁中道则重新回到三唐。在《蔡不瑕诗序》中,袁中道提出“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并申明自己的过去的诗歌“破胆惊魂之句,自谓不少,而固陋朴鄙处,未免远离于法”,近年始细读盛唐人诗,间有一二语合者。袁中道劝告袁祈年、彭年等“当熟读汉、魏及三唐人诗,然后下笔,切莫率自朎臆,便谓不阡不陌,可以名世也”,袁中道提出的诗学道路是“取汉、魏、三唐诸诗,细心研入,合而离,离而复合,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之神,则善矣”。在《淡成集叙》、《寄曹大参尊生》等文中,袁中道甚至批评杜甫、李白“发泄太尽”,而认为“天下事,未有不贵蕴藉者,词意一时俱尽,虽工不贵也”,显然他是在借评泊古人,而矫正当前的诗学风气。
钟惺所谓的“真诗”,完全出于他自己对古人的理解。他在《古诗归序》中说: 求古人之真诗。……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钟惺论“真诗”,偏重于主体的精神和心境,因此与格调派不同;他所谓“幽情单绪”,是偏于凄清孤幽的“寒蛩之吟”,与公安派的轻狂疏荡显然有别,钟惺《放言小引》云:“胸中真有故,而能言其所欲言,即所谓中伦之言,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者是也。苟无所本,而以无忌惮之心出之,则处士横议而已,诐淫邪遁,皆横之属也。”所谓“无忌惮之心”云云,就是指公安派的疏狂。实际上可以说,钟惺的“真诗”观是对格调、公安派诗学的反思,为了矫正二者之弊而提出的一种诗学理论。
钟惺“真诗”论的特征,首先是“深情”,钟惺《陪郎草序》曰:“夫诗,道性情者也。”诗要“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而非为写诗而写诗。 其次,“真诗”源自慧性。用“慧”论诗,是晚明诗学的重要特点。指主体超越外物羁绊以后,领略、观照外物和内心时表现出心灵审美的敏锐性。主体只有从烦杂的世俗生活中超脱出来,才能保持这种灵明敏锐性,所以钟惺说“清则慧”。 第三个特征,即深幽孤峭、静好柔厚的审美风格。钟惺是在阐述一种远离嚣世、穆静幽淡、闲旷游逸的生存状态。在钟惺看来,这才是诗人的生存状态,这样的诗人诗作才称得上“清物”二字。诗以静好柔厚为教,是钟惺关于诗歌风格论的新见解,当然其本意不仅仅是诗歌风格,更重要的是以一种“退然默然”的人生为基础的。
“厚”是钟惺后期诗学标举的重要诗学范畴。钟惺其人“影抱羸骸寒似梅”,其诗“最入幽微处”[1],有冰雪之气沐浴其间,他欣赏寒士之吟,他《诗归》中也表现出对尖新纤仄诗风的偏好,在总体倾向上呈现出寒俭之态。当时就有蔡复一提出批评:“《诗归》中有太尖而欠厚雅者,宜删去一二。”[2]钟惺对“厚”的强调,也是对自己前期审美偏向的自我纠正。 [1] 谭元春《丧友诗三十首》其十、二十二。 [2] 谭元春《鹄湾文草》·《奏记蔡清宪公(其四)》引蔡复一与谭元春书中语。
厚可以作浑厚、深厚、淳厚解,也即上文所谓“静好柔厚”。从“读书养气以求其厚”一语看,“厚”是以诗人的学识根底和道德境界为基础,是这种主体胸襟学识在诗风上的体现。诗人生活中读书养气与审美感悟的关系,读书养气不是直露于诗,而是通过对审美心灵的充实和提升,在审美感悟中体现出来的,因此说“厚出于灵”。而在创作中没有读书养气的基础,仅仅凭审美感悟,就不能达到厚的境界,因此说:“灵者不能即厚。”诗人的学识根底和道德修养不能滞塞其艺术感受力,故曰“必保此灵心”。但作诗若纯任灵心感悟,不免显露机巧狭局,这就是清新而未免有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