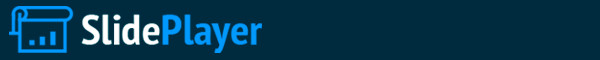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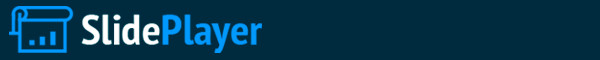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一般界定成「應用經濟學方法論研究政治科學的一門學問」,其中心思想是認定人類行為具自利動機(self-interest motives)且可以用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加些刻畫。 公共選擇的先驅可以追溯到兩位法國數學家Jean-Charles de Borda(1781)和Marquis de Condorcet(1785)。不過,這門學問的現代開展,則歸源於Duncan Black(1948a-c)的「中位者投票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和Kenneth Arrow(1950,1951)的「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
1. Arrow, 1951,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2. Downs,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3. Buchanan 和 Tullock, 1962,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4. Olson,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5. Niskanen, 1971,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表2-1 Condorcet paradox 甲 乙 丙 a b c b c a c a b
任何民主社會的集體決策必須滿足一些標準或要求,Arrow (1951)訂下幾個低標準的條件: (1)允許社會成員有各式各樣的不同偏好。 社會成員間有不同看法或偏好似乎是任一社會、特別是民主社會的常態。 (2)如果社會每個成員都一致認為a案比b案好,則社會偏好即應是a案比b案好。 這一條件用經濟學術語來說,即是必須滿足柏瑞圖準則(Pareto criterion)。 (3)社會成員有人認為c案比d案好,有人認為d案比c案好,如果社會對c和d兩案得到某一偏好排序,則此一社會偏好排序不會因為另一e案的出現或社會成員對e案評價的改變而改變。 例如,中國人社會有人認為蔣介石比毛澤東偉大,有人認為毛澤東比蔣介石偉大,中國人社會對於蔣介石和毛澤東誰比較偉大的排序,不會因為李登輝的出現或對李登輝評價的改變而改變。此一條件在文獻上稱為Independence from Irrelevant Alternatives,因為中國人社會在排序蔣介石和毛澤東誰比較偉大這件事上,李登輝是不相干的,也因此,李登輝的出現或中國人社會對於李登輝評價的改變,不應該影響中國人社會對於蔣介石和毛澤東誰比較偉大的排序。 (4)社會偏好排序不能以某一社會成員的偏好為偏好。 如果社會偏好排序以某一社會成員的偏好為偏好,則該社會即是獨裁社會。
著名的Arrow不可能定理在上述四個看似相當低標準的條件下,證明:如果社會成員有三個以上,選擇方案也有三個以上,則找不到任何機制可以保證將社會成員的個人偏好轉成同時滿足上述四條件具有一致性的社會偏好。所謂具有一致性的社會偏好,簡單瞭解即是不會發生Condorcet paradox者。 Arrow不可能定理說明,和Condorcet paradox相連的簡單多數決並不是關鍵,因為任何非獨裁機制(包括簡單多數決)都不能保證將社會成員的個人偏好轉成具有一致性的社會偏好。經濟學一般假定社會成員的個人偏好具理性,但理性的個人偏好卻如Condorcet paradox事例所示,可能帶來非理性不具一致性的社會偏好,此非理性的社會偏好,Arrow不可能定理證明,世上沒有任何合理機制能夠保證它不會發生。
效用 甲的效用函數 單維議題(例如教育支出水準) a 圖2-1 單維議題、單峰偏好 在議題單維且偏好具單峰的假定下,Black提出了著名的「中位者投票定理」(”median-voter theorem”):假設議題單維且社會成員的偏好全是單峰,則依社會成員效用最高的點排序,排序中位者最喜歡的議案,將在議案兩兩多數決對決下擊敗所有其他議案。
效用 乙 丙 甲 單維議題 a b c 圖2-2 中位者投票定理
如果存在一議案,能在議案兩兩對決下取得多數擊敗所有其他議案,此一特別議案文獻稱為”Condorcet winner”。存在Condorcet winner即不會出現Condorcet paradox的現象。
Plott (1967) i的無異曲線 y yi xi 圖2-3 二維單峰偏好 x
y b (乙) d a c (甲) (丙) x 圖2-4 d不是Condorcet winner
y c (丙) b (乙) a (甲) x 圖2-5 b是Condorcet winner
(戊) e c (丙) b (乙) a (甲) d (丁) 圖2-6 b是Condorcet winner
社會成員偏好的幾何排列形狀如圖2-5的情形顯然是特例而非常態。更進者,想像5人社會成員的情形,則Condorcet winner存在的情形,其幾何圖形必須如圖2-6所示,圖中,乙所最喜歡的b議案將為Condorcet winner,但注意其成立條件比圖2-5的情形更嚴苛,b案在兩個方向上都必須是中位投票者。當社會成員多於5人時,不難想像Condorcet winner必須在多個方向上都是中位投票者的情形。 由於如圖2-5和2-6所顯示,二維空間以上中位投票者定理成立的條件實在太過於嚴苛,因此,Black中位者投票定理一般只能應用於一維議題的分析討論上,也因此,其應用範圍有相當限制性。
,這一提案有其公平性,但卻可以由北、中二 ( 多數決所擊敗。 想像有一小鎮獲得上級補助款100萬元,小鎮有北、中、南三區,另假設小鎮有一民意代表機關,由分別代表北、中、南三區的三位民意代表所組成。如果分配100萬元的提案,由三位民意代表進行多數決的表決,結果會是怎樣?以(x,y,z)且x+y+z=100代表分配於北、中、南三區的提案。首先,考慮三地區平均分配的提案 ( ,這一提案有其公平性,但卻可以由北、中二 區民意代表聯合的另一提案(500, 500, 0)多數決所推翻擊敗。但(500, 500, 0)也非最後勝利者,因為它可以由北、南二區民意代表聯合的提案(700, 0, 300)多數決所擊敗。當然,(700, 0, 300)也非最後勝利者,因為他可以被最早的提案 McKelvey (1976)
McKelvey的發現告訴我們,當Condorcet winner不存在時,誰掌握投票程序即實質上掌握了投票結果。另外也告訴我們,投票程序不同,投票結果即可能不同,因此,最終投票結果如何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或不可預測性,而投票結果所代表的意義也變得不清不楚。
McKelvey的發現引伸出好幾個重要後果。第一,當不存在Condorcet winner時,投票議題可能是無窮盡的反覆循環而沒有均衡穩定解存在;第二,控制投票程序顯然相當重要,因為投票結果取決於投票程序,也因此,社會成員有動機誘因想取得投票程序的控制權;第三,到目前為止,所有討論都假設社會成員會根據其真實偏好投票(sincere voting),例如某甲認為a案比b案好,則a案和b案對決時,甲即會投a案一贊成票或投b案一反對票。但當投票程序會左右投票結果時,社會成員不一定會根據其真實偏好投票,所謂「策略性投票」(”strategic voting”)或是更為有利。底下,以美國歷史著名的Powell amendment為例子來作說明。
表2-2 Powell amendment 贊成或反對修正案 (不補助vs.修正案) (原案vs.修正案) 贊成票 反對票 總票數 132 97 229 67 130 197 199 227 426
策略性投票行為不僅見於國會或立法院,一般選民投票時也可能有策略性行為,台灣選舉的棄保效應即是例子。某選民喜歡王建遠超過馬英九,但台北市長選舉時該選民卻可能棄王保馬。因為王建根本沒有勝算,而馬英九和陳水扁卻併鬥激烈,勝負似乎相差無幾,也因此,何必浪費選票投給沒有勝算的王建。 公共決策的好壞良劣有賴於正確資訊的收集,但正確資訊是分散於社會不同成員身上,有沒有辦法找到機制保證社會成員會提供正確資訊而不是策略性的提供不正確的資訊(例如明明喜歡王建遠遠超過馬英九,但投票時卻投給馬英九而非王建)?Gibbard (1973)和Satterthwaite (1975)告訴我們另一個著名的不可能定理:假設社會成員有三人以上,選擇方案也有三個以上,另假設社會成員的偏好可以各式各樣,則找不到非獨裁式的機制保證社會成員會提供正確訊息。
民主社會的公共決策必須立基於公民的看法或想法,但公民的看法或想法是分散於社會不同成員身上(喜歡王建或馬英九,只有公民本人最清楚),社會不同成員的真實看法可能真實反應嗎?Gibbard-Satterthwaite不可能定理告訴我們,世上找不到一套機制能保證社會不同成員會真實反映其看法。 民主社會的公共決策必須立基於公民的看法或想法,有沒有可能將社會不同成員的不同看法或想法加總成具一致性的社會看法或想法,而不會發生像Condorcet paradox的情形呢?Arrow不可能定理告訴我們,世上找不到一套機制加總社會不同成員的不同看法而保證不發生像Condorcet paradox的情形。 Arrow不可能定理是在社會成員真實偏好已知下,討論個人偏好加總成社會偏好的不可能問題;而Gibbard-Satterthwaite不可能定理則是討論獲取社會成員真實偏好不可能的問題。此兩大不可能定理對政治經濟學研究投下極大的負面因素,的確,1970年代,不少學者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前景抱持悲觀態度。但從1970年代末期,尤其是1980年代開始,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開始有了大轉折。
Vickrey-Groves-Clark機制 在Arrow不可能定理的世界裡,Condorcet paradox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現象;而McKelvey所發現的世界,政治是非常的不穩定,政策隨時可能有極大的轉變。但Tullock (1981)問了一個關鍵問題:為何現實世界觀察的政治或政策,不是像理論世界所描述般地呈現高度不一致或不穩定呢?針對此一提問,學者開始逐漸認識到,現實世界的政治已發展出複雜的制度規章限制了多數決的不穩定運作,並由此帶來了政治均衡或穩定。 Shepsle(1979)
Shepsle將Arrow不可能定理轉成可能的路徑是從限制投票運作的制度下手,而不像Black的中位者定理是從限制選民的偏好下手。像Black限制偏好下所帶來的政治均衡,文獻稱”preference-induced”均衡,而像Shepsle從政治制度結構下手所帶來的政治均衡,文獻稱”structure-induced”均衡。 agenda setter模型(Romer和Rosenthal 1978, 1979),majoritarian bargaining模型(Baron和Ferejohn, 1989),和lobbying模型(Grossman和Helpman 1994, 1995)。這些模型或多或少都是從認識到民主制度不等同於簡單多數決下手,推導得政治穩定均衡,從而將Arrow不可能定理轉成可能。不過,這些”structure-induced”均衡的模型互相差異頗大,多少說明一般理論似乎不容易建立。 這類均衡文獻稱為「制度均衡」(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制度均衡是在制 度外生給定下導得的政治均衡,但制度內生下的「均衡制度」(equilibrium institution)為何,則仍缺如。
國會投票 open rule和closed rule 圖3-2 委員會和大會希望議題移動方向相同 圖3-3 委員會和大會希望議題移動方向相反 1 x0 xm x1 圖3-2 委員會和大會希望議題移動方向相同 xm x0 xc 1 圖3-3 委員會和大會希望議題移動方向相反
利益團體的政治捐獻無論國內外,金額都相當龐大,這些利益團體的捐款究竟是想買什麼呢?一般人的看法可能是,這些捐款想購買對利益團體有利的政策,但實証研究卻發現,利益團體的捐款大小和定案政策之間關聯性似乎並不明顯。一個可能解釋是,如果國會議員公然投票支持利益團體支持的法案,將容易引起選民的反感反彈。但國會委員會制度賦予委員會的”gate keeping”和”monopoly proposal”權力,卻使國會議員能暗中使力幫助利益團體:委員會可以讓對利益團體有利的法案被提出而不被大會修正;不利利益團體的法案,委員會可以加以阻隔讓它沒機會提出表決。這些暗中使力幫助利益團體的動作較不明顯,因此,也較不容易引起選民的反感反彈。
為什麼國會投票規則中有closed rule的設計?一種說法是,這種制度設計方便國會不同委員會的成員之間進行利益交換,也方便和不同利益團體之間進行利益交換,如果投票規則是open rule而不是closed rule,則個別委員會將不會擁有巨大權力,由是,個別委員會之間、不同委員會和不同利益團體之間也就沒有什麼利益可供交換[1]。Krehbiel(1991)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法案施行後的好壞結果如何,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因此,有賴國會議員的專心研究提出優質法案以解決或降低此不確定性,而closed rule投票規則是讓委員會成員成為該委員會管轄事項專家的必要之惡,試想,如果委員會的提案,大會可以用open rule投票規則將其亂修、大修一通,則相信委員會成員將不會有心投入時間、精力研究其管轄事項的法案。
1. 白吃問題 有共同利益的人會組成利益團體追求其共同的利益,而藉由不同利益團體的互動、討價還價所產生的政策具有多元性質,反映包容所有不同利益團體的不同利益。這是傳統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的中心觀點,此一觀點隱含現實政策具備有多元良好性質。 Olson(1965)的鉅著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予以上述政治多元論致命一擊。團體追求的 共同利益,就團體的個別成員而言是一公共財,讓別人去拼命努力,自己坐享其成的白吃問題(free ride)於焉產生,這猶如一個和尚挑水喝,3個和尚沒水喝的道理。因此,即使某些人之間存在共同利益,但這些人未必能克服白吃問題成功地組成團體去遊說反映其利益,結果是,現實政策往往沒有反映一些團體的利益,也因此,政治多元論認為現實政策具備有多元良好性質的論點似乎不能成立。 克服白吃問題,Olson認為大團體面對的困難比小團體大得多。小團體由於成員少,成員之間較容易互相認識,因此,成員之間相互推動參與團體活動的力量較大;另外,小團體個別成員是否作出貢獻,對團體活動成敗影響較大,且因為團體成員少,誰有作出貢獻誰沒有作出貢獻較容易被知道;小團體成員之間由於成員人數較少,也比較容易有長期互動的關係存在。這些種種都造成小團體相對於大團體在反映、遊說其利益上有其優勢性,的確,消費者相對於生產者似乎總是一盤散沙,而工人相較於資本家也似乎來得較不團結。 上述大小團體在克服白吃問題上的不對稱現象,Olson認為也存在於個別團體內部。如果某一團體內部的組成成員大小有別,這反而有助於該團體達成其團體的共同利益,這是因為小成員的參與否可能不具關鍵性,而大成員是否參與作出貢獻,對團體利益的達成則相當關鍵。團體內部成員大小不一雖有助於團體達成其目標,但同時也造成大被小欺的現象,不少研究顯示,北約組織中的美國和華沙公約組織中的蘇聯,其經費負擔遠遠超過其應該負擔的份額。
1. 副產品理論 大團體面對嚴重的白吃問題,但成功的大團體集體行動為什麼三不五時還是會出現呢?Olson的解釋是其著名的副產品理論。大團體純粹以團體共同目標的達成來誘引團體成員的參與將有其困難度,但它可予以參與團體行動的成員才能享有的一些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s)來誘引團體成員參與集體行動,例如,參與反核示威遊行的人可以得到印有反核字樣的T-shirt一件,得到這件T-shirt的人可以向他人炫耀證明他的確參加反核示威遊行,由此得到個人的滿足感,這一滿足感是私人利益,和反核運動之間沒什麼直接關聯性,但藉此可能誘引許多人參加反核示威大遊行。藉由發給反核T-shirt成功地辦到反核示威大遊行,因此,反核示威遊行是發給T-shirt此一選擇性誘因在克服白吃問題下所帶來的副產品。提供選擇性誘因的另一典型例子是工會要求雇主禁止雇用非工會的員工,不少研究顯示,當這一選擇性誘因機制被採用時,參加工會的員工人數會比較多,而工會工人賺取的工資也會比較高。
投票矛盾性 Olson的副產品理論能解釋像美國的民權運動、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的崩解、或是中國文化大革命般的大規模集體行動嗎?不少人對其充分解釋能力抱持懷疑。 大選區的投票行為基本上也是Olson理論的範疇。陳水扁對扁迷而言是一公共財,因此,去不去投票支持他也會面臨Olson所論述的白吃問題。但在如總統選舉的大選裡,一票實在無足輕重,有人估算過,總統大選中,你手上一票能決定輸贏的或然率,和你去投票所的路上被汽車撞到的或然率相當,在這麼微小的或然率下,扁迷手上的一票完全決定不了阿扁是否當選的命運,因此理論預測,理性計算下,大半扁迷不會去投票,但實際情形卻不是如此,此理論預測和實際結果互相矛盾的現象,文獻稱之為「投票矛盾性」(”voting paradox”)。 有些學者企圖引用賽局理論解決投票矛盾性。如果每個人都認為一票無足輕重而不去投票,則去投票的人即可以一票定江山,因此,賽局下的均衡投票率應是高於零。不過這一研究路徑並沒有真正解決投票矛盾性,在一篇重要文章中,Palfrey和Rosenthal(1985)證明,當考慮入現實的訊息因素時,大選區賽局下的均衡投票率仍然是接近零。
相關投票矛盾性的另一重要問題是,大選下,選民會花多少時間、精力去蒐集和其投票相關的訊息。Downs在他1957年的名著中提出一個直到今天仍令人驚動的論點:「理性的無知」(“rational ignorance”)。大意是說,由於選民一票無足輕重、無法撼動選舉結果,因此,理性的選民不會花費時間、精力去瞭解候選人端出的「牛肉」。作為一位消費者,購買汽車時,會考察不同車種的性能,請教親戚朋友的意見,到好幾家汽車經銷商去試車,甚至有人會去閱讀相關汽車的專門雜誌。簡言之,買車過程會花去不少的時間、精力、金錢,不過這些花費值得,因為多花費會讓消費者買到較好較便宜的車子。選舉總統,對你我命運的影響不下於、甚至高於挑選購買一輛汽車,但作為一位選民,會花費時間或是精力去瞭解候選人的「牛肉」嗎?Downs的答案是否定的,畢竟一票無足輕重,完全決定不了你的命運。你我手中一票可能「神聖」,但Downs告訴我們,那是「無知」的一票。Downs論點的弔詭在於,選民的無知,是選民自己經過理性思考、精打細算下的結果。 Brennan和Buchanan(1984)一文把「選舉」類比成「球賽」,兩對主帥、副將精銳盡出,犯規動作頻頻,觀眾席上兩隊球迷掌聲、噓聲四起。選民投票的目的或許就猶如球迷般表達對「偶像」不同的看法罷。
最適投票通過比例 Wicksell(1896)從公共財角度出發,認為公共財提供利於全體國民,因此,理論上應該可以找到一提供水準和成本分攤方式令全體國民沒有人會因公共財提供而受害,而要達到此一柏瑞圖增進(Pareto improvement)的結果,投票採取一致決或無異議通過(unanimity rule)是必要的。不過,採取此一投票規則在現實政治上遭遇兩大困難:第一,要找出一個令各方滿意沒有人反對的議案可能相當耗時費力,此一成本可能超過議案本身所帶來的利益;第二,一致決投票等於賦予每個國民否決權,如此,無疑鼓勵個別國民採取策略式行為,不斷進行否決以謀取從議案中獲得更大利益。現實政治少有採取一致決無異議的投票方式。 現實政治並不是所有的公共決策都訴諸簡單多數決,而實際上,簡單多數決也未必是最恰當,有些問題對於個別國民影響巨大、太過於重要,不能輕易地以簡單多數決來作決定,另有些問題則對個別國民影響輕微不甚重要,每次都訴諸簡單多數決表決,無此必要,甚至授權行政單位自行裁量即可。但怎樣的多數決是最適又如何決定呢?關於此一問題的最早分析見於Buchanan和Tullock 1962年的名著The Calculus of Consent,其分析焦點在於choice of rules的憲政問題而不是choice within rules的一般政治問題。這兩位作者從個人角度出發,想像個人對最適投票通過比例此一憲政問題會作如何思考。
Buchanan和Tullock把政治決策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屬於憲政問題,憲法中明定各類議案所需要獲得通過的投票比例,第二階段則以憲法中明定的投票比例應用於不同類公共決策的議案。為避免特定議案上個人的偏私,Buchanan和Tullock假定當制訂憲法時,個人對將來某特定議案所可能採取的立場或偏好完全無知,即最適投票通過比例的憲法層次決定是在無知面紗(veil of ignorance)下進行。
Buchanan和Tullock以兩個函數來分析最適投票通過比例的決定。一是外部成本函數(external cost function),一是決策成本函數(decision-making cost function),前者指通過某議案對反對者所加諸的傷害成本,後者則指為通過某議案尋求議案折衷協調取得多數決所花費的時間、精力成本。外部成本是議案通過所需投票比例的遞減函數,如果投票採比例最高的一致決,則因為任何人不會投票贊成對其造成傷害的議案,外部成本將為零。決策成本是議案通過所需投票比例的遞增函數,因為所需投票比例愈高,議案獲得通過所需花費折衷協調的時間精力成本也將愈高。最適多數決即是在上述二成本中作取捨替換,取決於外部成本和決策成本加總最低者,如圖6-1的n點。 外部成本+決策成本 決策成本 外部成本 1 n 圖6-1外部成本和決策成本
如果某類議案本質上意見紛歧取得共識不易,但究竟採取那一議案對個人福利影響有限,此種情形可以將其想成決策成本函數上移,外部成本函數不動,於是由二成本函數決定出來的最適多數決將低於n;反之,如果某類議案本質上關係到個人的基本權利,剝奪權利個人福利損失巨大,然而該議案決策成本卻不高,此種情形可以將其想成外部成本函數上移,但決策成本函數不動,於是由二成本函數決定出來的最適多數決將高於n。 Buchanan和Tullock的分析告訴我們,怎樣的投票通過比例是最恰當,要看議案性質所引發的外部成本和決策成本而定。
代議方式 現實世界投票規則各式各樣,現實世界民意代表選出來的方式也有許多不同式樣。三種常見的代議方式: (1) first past the post (FPP):每位選民手上有一票,全國分成許多選區,各選區只選出一位民意代表; (2)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每位選民手上有一票,全國分成許多選區,但同一選區選出多位民意代表; (3)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每位選民手上有一票,全國只有一選區,選民選黨不選人,各黨民意代表人數依其獲取選票比例分配。 英國和許多其先前殖民地採用FPP(如美國、印度和加拿大);韓國國會議員選舉採用SNTV,台灣和日本過去國會議員選舉也採用此一制度;PR是比例代表制,但目前真正採用此代議制的只有以色列和荷蘭,其他大半採取某類混合制,例如,當今日本國會議員選舉採取FPP和PR的混合制,另台灣立法委員選舉採取SNTV和PR的混合制。
不同代議制可以兩大面向來瞭解:代表性(representation)和運作順暢性(governance),強調前者傾向視政府為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強調後者則傾向視政府為responsible government。這兩面向常存有衝突,例如,最具代表性的代議制是讓每個人都成為議員,但如此一來,議會議事運作相信會非常不順暢;反之,意見相同的人所組成的議會,議事運作相信會順暢多多,但其代表性則會相對不足。 強調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的代議方式(如PR)較有利於小黨,而強調responsible government的代議方式(如FPP)則較有利於大黨。文獻上有所謂Duverger’s law,認為FPP代議制度將會帶來兩黨政治,在FPP下,第三大黨生存不易,因為不論選民投票或利益團體捐款,都不會將其浪費在沒有勝選機會的第三大黨身上。實証發現高度支持Duverger’s law。
怎樣的代議制會產生中間路線的民代?又怎樣的代議制會產生各式各樣多元路線的民代?Cox (1987, 1990)對問題進行分析,他認為小選區或大選區具關鍵性。Cox研究發現,如果同一選區選出的民意代表人數多(大選區),則比較容易產生各式各樣多元路線的民代。Cox以過去日本眾院採用的SNTV為例,日本眾院議員選區選出人數大半是3到5人,也因此,不容易產生中間路線的民代,相反地,容易產生各式各樣甚至採取極端立場的民代。但各式各樣甚至極端立場的民代卻是社會的縮影,具有代表性,但議事運作會較不順暢。反之,像FPP同一選區選出的民意代表只有一人(小選區),極端立場民代不容易選上,中間立場民代會勝出。中間立場的民代未必是社會的縮影,可能不具有社會代表性,但大半由中間立場民代所組成的議會其議事運作將會較順暢。
和PR制相比,FPP制常會造成代表多數民意的民代其代表人數過多和代表少數民意的民代其代表人數過少的問題。例如以20世紀後半美國眾院選舉為例,研究顯示眾院多數黨獲得的席次大大超過多數黨獲得的票數,另2001年英國大選自由黨獲得的票數比有18.2%,但其議員的代表席次卻少於8%。 小選區像FPP制,第三勢力不容易生存,因此,各方力量會設法在選前進行整合成兩大勢力(Duverger’s law)。大選區像SNTV制,小黨獨立候選人相對容易生存,各方力量不會在選前進行整合,因此,意見整合只有留待選後進行。大選區選後才整合的特點,多少說明台灣的立法院為何似乎總是爭鬧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