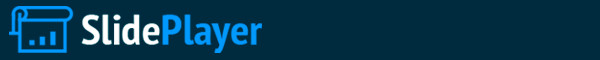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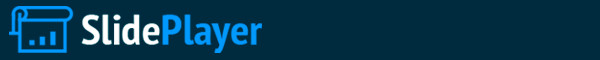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中国法律史 导言
夏代的“禹刑”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总称、泛称。《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这里所说的“禹刑”,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而是泛指夏朝的法律与刑罚。“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应该理解为在夏朝建立以后,为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制定了法律,适用了刑罚。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我们现在无法确切地说明夏朝的法律究竟有多少、详细内容是什么。但根据早期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判断夏朝的法律已经有较大的规模。
夏代的罪名与刑罚 从散见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到,夏代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诸如“不孝”、“不友”、“不用王命”、“失天时”等一些比较稳定的罪名。同时也形成了以“五刑”为主要内容的比较成熟的刑罚体系。 所谓“五刑”,是指在中国早期社会中经常使用的五种刑罚,即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五种刑罚。这五种刑罚由轻至重,构成了中国早期比较完备的刑罚体系。 如墨刑,又称黥刑,是在罪人面部或额头刺字,并染上墨,作为受刑人的标志。所以,墨刑即是刻人肌肤的身体刑,又是使人蒙受耻辱、以区别与常人的耻辱刑。墨刑是五行中最轻的一种。
夏代的监狱 根据史籍记载,夏代已有了正式的监狱,称为“圜土”。“圜土”愿意是指圆形的土坑或土墙。夏代的监狱以“圜土”为名,说明还比较简陋。
商代及其文化
商代“汤刑”与罪名 《左传》记载说:“商有乱政,而作汤刑”。这里所说的“汤刑”,是商朝法律的总称,泛指商朝的法律法令和刑罚。“汤刑”也不是一部成文的法典。在商朝的法律规范中,不成文的习惯法仍占有很大的比重。 另外,国王发布的“命”、“诰”及“誓”也是当时重要的法律渊源,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商代甲骨文以及其他文献资料均证明,商朝的刑法在夏朝刑法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罪名已明显多于夏代,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如“舍弃稼事”、“不从誓言”、“颠越不恭”、“不有功于民”等等。对于各种犯罪的处罚,相应也更加具体和详细。
商代的刑法制度 主要还是沿用夏代以来的墨、劓、剕、宫、大辟等五刑,作为常用的主体刑罚。在甲骨文中,已有关于墨、劓、刖、宫的记载,说明“五刑”在商朝应用已经十分广泛。在商朝,五刑中的大辟即死刑的方法更是多种多样,且日趋残酷。 特别是在商朝末年商纣王统治时期,还出现过炮烙、醢刑、脯刑等著名的酷刑。
西周法律制度
武王罚纣
利簋与武王克商 武征商隹甲子朝歲 鼎克昏夙有商辛未 王在管师赐有事利 金用乍檀公寶尊彝 利簋通高28、口径22厘米,敞口,深腹,方座,双耳垂珥,腹部与方座均以云雷纹为地,主体花纹为饕餮纹,方座之四角饰蝉纹。圈足以云雷纹为地,主体花纹为蘷龙纹。器内底铭文四行三十二字。 武征商隹甲子朝歲 鼎克昏夙有商辛未 王在管师赐有事利 金用乍檀公寶尊彝 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同坑出土铜器151件,利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以德配天” 在夏、商两代“天讨”、“天罚”神权法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理论,构成在中国早期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天道”观念。 西周统治者提出,“天命糜常”,“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人间君主一旦失去应有的德性,就会失去上天的保佑与庇护,天命随之转移,新的有德者就会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奉上天之命来统治万民的人间君主,应该“敬德”、“明德”,“以德配天”,才能真正保有天命,并得到上天的保佑和庇护,从而使国祚绵长。而“德”的要求,包括三个基本方面:敬天、敬宗、保民。要求统治者恭行天命,尊崇上天与祖宗的教诲,约束自己的欲望和行为,爱护天下的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 在中国史上,“以德配天”理论的提出,是政治理论上一个巨大进步。从夏、商时期主张“天讨”、“天罚”,单纯“敬天”,发展到西周时期“以德配天”,除继续强调天命外,也对统治者提出道德上的要求,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明德慎罚”的法律主张 在“以德配天”的政治理论之下,西周统治者还进一步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主张。所谓“明德”,就是主张崇尚德治,提倡德教。用道德的力量去教育、感化,使天下臣服;所谓“慎罚”,就是主张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审慎、宽缓,不应“乱罚无罪,杀无辜”。“明德慎罚”主张的具体要求可以归纳为“实施德教,用刑宽缓”,实际上就是强调将教化与刑罚相结合。在“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理论体系中,“实施德教”是前提、第一位的。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主张,代表了西周初期统治阶层的基本政治观点。这种法律思想影响极为深远。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原则。西汉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主张被儒家学派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法律思想和法制方针,成为中国古代最具影响的一种法律观念。
“吕刑” 第五代周王穆王时,为革新政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在法律方面,就是命令吕侯“作吕刑”。因吕侯又称“甫侯”,所以所作之刑也称“甫刑”。 此次吕侯所作“吕刑”的具体内容已无法考证,但在记述中国上古时期历史的重要著作《尚书》中,有《吕刑》一篇,记载了此次穆王命吕侯进行法律改革的大致情况。 《尚书》中的《吕刑》一篇,既不能看成是一部成文法典,也不是此次法律改革的直接成果,而是关于这次法律改革的历史记录。
“礼”的渊源与发展 作为一种言行规范,“礼”最早源于氏族时代的祭祀风俗。在阶级明显分化、国家形成以后,一部分反映等级差别和专制要求的精神原则逐渐从具体的礼仪形式中被抽象、概括出来,形成了一系列指导阶级社会生活的原则和规范,即“礼”的抽象原则;而那些带有象征意义的各种礼仪,则仍保留在制度层面发挥作用。 根据史籍记载,在夏、商时期,作为言行规范的“礼”就已经存在。孔子就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说明在夏、商、西周的礼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特别是在西周初年,经过“周公制礼”以后,周礼成了一个庞大的“礼治”体系,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广泛的调节作用。
周礼的性质与作用 先秦以后,许多中国古代文献典籍都有对周礼作用的描述评价。《礼记》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祭祀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可见,在西周时期,在国家行政、司法、军事、宗教、教育,乃至伦理道德、家庭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礼”的调节和规范。 一般而言,“礼”大体上包括抽象的精神原则和具体的礼仪形式两个层面。作为抽象的精神原则,诸如“忠”、“孝”、“节”、“义”、“仁”、“恕”等,都是“礼”的基本内容。从精神原则方面看,“礼”的核心在于“亲亲”和“尊尊”,在于强调等级名分、等级差别。从具体的礼仪形式方面看,“礼”通常有“五礼”、“六礼”和“九礼”之说。
西周时期的“礼”与“刑” 西周时期的“礼”与“刑”都是当时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规则。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西周社会完整的法律体系。 其中,“礼”是积极、主动的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刑”是消极的处罚,是惩恶于已然的制裁。也就是说,“礼”总是从正面主动提出要求、对人们的言行作出正面的“指导”,明确要求人们应该作什么、不应该作什么,可以作什么,不可以作什么; “礼”的功能,重在“教化”。“刑”则相对处于被动状态,对于一切违“礼”行为,进行刑罚处罚。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刑”的功能,重在制裁。
“三赦之法” 西周时期有“三赦之法”: “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 对于这三种人,如果触犯法律,应该减轻、赦免其刑罚。
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 西周时期,观念上和制度上已经开始对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惯犯与偶犯进行明确的区分,给予绝然不同的处罚。 据史籍记载,当时有“三宥之法”,对三种情况下的犯罪要宽宥、原谅:“一曰过失,二曰弗知,三曰遗忘”。这种制度说明当时对于过失犯罪、对于犯罪人主观恶性上的差别,已有较清楚和深刻认识。 在一些先秦典籍中,还有关于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记载。如《尚书·康诰》中载:“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时乃不可杀。”其中,“眚”是指过失之意,“非眚”即是故意。“惟终”是指惯犯,“非终”则是指偶犯。
罪疑从轻、罪疑从赦 “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是中国上古时期、夏以前关于疑罪从轻的记载。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审慎用法,有极为悠久的传统。 西周时期,为保证适用法律的谨慎,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和推行“罪疑从轻”、“罪疑从赦”的原则,对于疑案难案,采取从轻处断或加以赦免的办法。《尚书·吕刑》载:“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这正是罪疑从赦原则的具体说明。 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还有“三刺之法”,凡是重大或疑难案件,要经过三道特殊的程序来决定:“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说明西周时期对司法审判,特别是重大疑难案件的慎重。“罪疑从轻”、“罪疑从赦”原则的推行,也是西周“明德慎罚”思想的具体体现。
西周时期“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 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在总结前代政治经验和用刑经验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刑罚世轻世重”理论,并以此作为刑事政策,来指导法律实践。 《尚书·吕刑》说:“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权”是权衡、度量。主张“刑罚世轻世重”,就是说要根据时势的变化、根据国家的具体政治情况、社会环境等因素来决定用刑的宽与严、轻与重。 具体的轻重宽严标准则是:“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所有权 《诗经》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几句话,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极端权力的充分概括。从理论上说,在中国古代,天子被认为是“上天之子”,代表着上天来统治人间。天下的所有一切,包括土地、人民,最终都归天子所有。所以,在西周时期,天下最为重要的两项社会资源——土地与臣民,在理论上都属于周王所有。 在西周时期,实行政治上的分封制。这种逐级分封、层层占有的政治体制,在实际上造成了西周时期所有权制度的分割,造成了西周时期对于土地、臣民的特殊的所有权形式。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在西周时期,除在土地、臣民等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特殊社会资源方面,所有权有所限制外,对于一些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动产和不动产,包括被看成是物产的奴隶,各级封建主乃至自由民,都拥有所有权,可进行交换。
西周债和契约 西周时期,随着私田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债权逐渐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大致有两类,一是因契约而产生的债,一是因侵权和损害赔偿而产生的债。其中,契约之债是主要的表现形式。与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民事契约关系的发展。据史料记载,西周时期的契约关系比以前有了较大的进步。 在当时,比较普遍的契约形式有两种,一种称为“质剂”,一种称为“傅别”。“质剂”是使用于买卖关系中的契约形式。其中,“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傅别”则是使用于借贷关系中的契约形式,乃是在一契券的正面、反面都书一大字,然后一分为二,借贷双方各执其一,以为凭证。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大量的关于买卖、借贷和租赁关系的记载。
西周时期婚姻的缔结与“六礼” 婚姻必须合乎一定的礼仪,这就是“婚姻六礼”。具体包括: (1)纳采,即男方请媒氏携礼物到女方家提亲; (2)问名,即在女方家长答应议婚后,男家请媒氏问明女子的生辰、身份,并卜于祖庙以问吉凶; (3)纳吉,在卜得吉兆以后,男家携礼物至女家确定缔结婚姻; (4)纳征,也称纳币,男家送财礼至女家,正式缔结婚姻; (5)请期,即男家携礼物至女家,确定婚期; (6)亲迎,即在确定之日,新郎至女家迎娶,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也最终成立。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对以后各朝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解除婚姻的条件与限制 据史籍记载,西周时期在解除婚姻方面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称为“七出三不去”。其中,“七出”又称“七去”,是西周时期男子可以休妻的七项条件。具体是指: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口多言去;盗窃去。所谓不顺父母(公婆)去,是因为“逆德”。无子去,是因为绝嗣不孝。淫去,是因为乱族 。妒去,是因为乱家。有恶疾去,是因为“不可共粢盛”,既因女方的疾病而不能共同生活。口多言去,是因为“间亲”。盗窃去,是因为“反义”。女子若有上述七种情形之一,丈夫既有正当的理由合法地休妻。
“三不去” 按西周时期礼制,女子若有“三不去”理由之一者,夫家即不能休妻。“三不去”具体是指:有所娶而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其中“有所取而无所归”是指女子出嫁时尚有娘家可回,但休弃时已无本家亲人可依。此时休妻将置女子无家可归的境地,故不能休妻。“与更三年丧”是指女子嫁入夫家后,曾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孝三年。如此则该女子已经对公婆尽子女之孝道,故不能休妻。“前贫贱后富贵”是指娶妻时贫贱,但以后变得富贵。按照礼制要求,“妻者,齐也”,夫妻应为一体。贫贱时娶之,富贵时休之,义不可取,故不能休妻。
审理案件的“五听”制度 通过长期司法经验总结,西周时期形成了审理案件的“五听”制度。所谓“五听”,是审判案件时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五种观察方式,按汉代人郑玄的解释: “辞听”是“观其出言,不直则烦。”就是观察当事人陈述时的语言表达,如果语无伦次,说明所言非实。 “色听”是“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就是观察当事人陈述时的面色,如果面红耳赤,就说明说述非实。 “气听”是“观其气息,不直则喘”,既观察当事人陈述时的喘息,如果所言非实,就会气喘吁吁。 “耳听”是“观其听聆,不直则惑”,即观察当事人的听觉,如果所言非实,就会听觉迟钝。 “目听”是“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既观察当事人陈述时的目光,如果所言非实,就会两目无光。 可看出西周时期已开始注意并能运用司法心理学的一些经验处理案件。除“五听”外,西周时期审判案件时也很重视证据的使用。
春秋时期的公布成文法活动 1.铸刑书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向全社会公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史称“铸刑书”。当时“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向全社会公布,是为了强调国家法律的尊严,同时有利于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贯彻执行。 2.竹刑 邓析是郑国的大夫,是一位与子产同时代的思想政治人物。他曾在郑国办私学传授法律知识,并经常帮助他人进行诉讼。公元前530年,邓析综合郑国内外的法律规范,编成刑书,刻在竹简上,称为“竹刑”。后来邓析因为政治纷争而被当政者杀害,但“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最终被官方接受,成为正式的法律。
春秋时期的公布成文法活动 3.铸刑鼎 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范宣子所著刑书刻在鼎上,公布了晋国的成文法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正式的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史称“铸刑鼎”。
春秋战国法律制度
《法经》的制定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它是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在总结春秋以来各国公布的成文法经验基础上制定的,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从战国初期开始,各诸侯国的统治集团为了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相继开展了以巩固和健全封建政治经济制度为目的的变法改革运动。其中,魏国李悝所进行的变法是最早也是比较成功的一次改革。李悝是战国初年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李悝曾担任魏文侯师及魏相等重要职务。主政期间,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社会改革。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巩固改革的成果,李悝“撰次诸国法”,即考察各国成文立法,总结各国经验,制定出魏国的重要法典——“法经”。
《法经》的主要内容 《法经》原文早已失传。《晋书·刑法志》等后代文献保存了《法经》的篇目及简略情况。 《法经》共分六篇:一为“盗法”,二为“贼法”,三为“囚法”,四为“捕法”,五为“杂法”,六为“具法”。 其中“盗法”、“贼法”是关于惩治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他人及侵害财产等犯罪的实体法规定。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法经》将“盗法”和“贼法”列在法典之首。“囚法”(也作“网法”)、“捕法”是关于追捕、囚禁及审讯罪人的法律规定,大多属于程序法的范畴。 第五篇“杂法”是规定贼盗以外其他犯罪的篇目,主要规定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徙禁、金禁等“六禁”的内容。 第六篇“具法”是关于从重从轻、减免刑罚等定罪量刑通用原则的规定,相当于后世法典中的总则部分。
《法经》的历史地位 《法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首先,《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 其次,《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帅、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在内容上,《法经》六篇的主要内容大都为后世封建法典所继承。
法家与变法
商鞅变法与秦国法制的发展 公元前359年,法家著名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改革,史称“商鞅变法”。这是战国时期在魏国李悝改革之后推行的一次内容更广泛、规模更宏大、影响也更深远的法制改革。 商鞅原姓公孙,名鞅,卫国人,后因在秦国变法有功,被秦孝公封于商,故人称商鞅或商君。商鞅自幼“好刑名法术之学”,青年时期曾在法家势力强大的魏国游学,深受发家思想的熏陶,很快成为法家思想的坚定的实行者。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招贤,商鞅挟《法经》入秦,得到秦孝公重用,在秦国推行意义重大的变法活动。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从法律的角度看,商鞅变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法为律,扩充法律内容; 二是运用法律手段推行“富国强兵”的措施; 三是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的特权; 四是全面贯彻法家学派“以法治国”、“明法重刑”主张。 其一强调“以法治国”,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宣传。同时要求全体臣民学法、明法; 其二实行“轻罪重刑”,用严酷的刑罚来扫除改革的阻力和障碍; 其三不赦不宥。为了贯彻重刑原则,保证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商鞅反对对各种犯罪者进行赦宥,主张凡有罪者均应受罚。 其四鼓励告奸,实行连坐。
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 商鞅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一次极为深刻社会革命。这次变法不仅给守旧势力以沉重打击,而且为秦国政治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秦国的封建法制也在变法过程中得以迅速发展。 虽然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反扑回来的旧势力车裂,但商鞅变法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制度、所推行的法律法令并没有消失。商鞅死后,商鞅变法的成果被秦国继承和发扬。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强盛起来,最终一举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