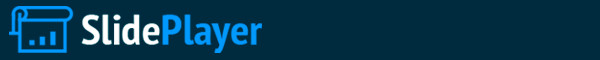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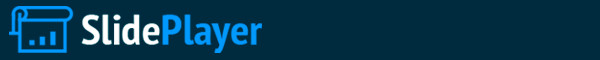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第七章教师的人格 第二节 教师人格修养的两大问题 第七章教师的人格 第二节 教师人格修养的两大问题 一、“取法乎上”的策略 二、教师人格修养的审美尺度
人格的形成一方面是特定文化,具体讲是一定社会规范、价值系统对个体的直接影响,使特定的人接受一定的伦理文化,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道德主体自身不断从客观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追求价值与人格的理想,从而实现其人格的改造和提升的过程。前者可以称作“模塑”过程,后者可称为“修养”的过程。前者是人格形成的基础,但后者却是人格形成的关键。修养之所以是“关键”,纯粹是因为没有没有修养的主观需要和努力,模塑就可能是无效的。
教师的人格修养也是这样。一方面教师个体会受到既定职业道德传统和客观存在的职业道德文化的影响,日久天长,在职业道德上他有一个被“模塑”或者说是社会化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的真实完成依赖于教师对教育事业及其道德要求的认识或领悟的程度,依赖于其道德义务感的不断养成和职业道德策略上的不断成熟,一句话,依赖于教师的人格“修养”。这里我们集中探讨教师人格修养的两个根本性的课题。一是修养的策略问题,二是修养的尺度问题。
一、“取法乎上”的策略 据1998年10月18日的《环球时报》报道,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学生问美国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Berkshire Hathaway公司总裁,《福布斯》杂志1998年公布的全球200名亿万富翁中名列第三)这位“比上帝还富有的人”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巴菲特回答提问时向大学生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选择一个你最钦佩的人,把你钦佩他的原因写下来。……然后,写下那个你最讨厌的人的名字,写下那个人身上使你拒其于千里之外的那些品质。我建议你们观察一下你们所钦佩的人的行为,使这种行为成为你的习惯;你们也要观察一下别人身上应受到斥责的东西,并下决心不犯同样的毛病。如果你们做到了这一点,你们将会发现,你们已能够开足你们所有的马力了。”[1]巴菲特所提的建议其实也可供教育工作者参考。 [1] 张允文译:《两个世界富豪的一次潇洒对话》,《环球时报》1998年10月18日,第14版。
我们这里所谓“取法乎上”的策略,指的就是教师的人格修养以价值和人格理想的确立为前提,高处着眼进行修养。在人格修养过程中,由于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要求过高、扼杀人性的曲折,所以特别强调道德目标上的现实性。但是现实化的粗俗形态就可能是否定理想人格现实性的世俗化。而一旦出现对理想人格和终极理想的真正否定,道德人格的修养就成为没有意义也没有可能性的东西。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策略问题,主要的理由如下: 1.人格修养的规律性 2.师范人格的特点(格位高) 3.中国古代的伦理智慧
1.人格修养的规律性 这里所谓的修养的“规律”就是指人格修养与终极信仰之间的必然联系。 这里所谓的“信仰”并非只指宗教信仰,而是指包括宗教信仰形态在内的所有对于终极价值的确信。其基本形态有三:宗教信仰、政治信仰、人生信仰。终极信仰与道德人格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证与聚合,二是圣化与提升。
何谓“论证与聚合”?我们知道一个人之所以有某种特殊的道德人格无非是因为他有一套外在的道德行为表征和内在的道德观念、情感、信念系统。而外在的行为表征之所以如此组合而且有一贯性乃是因为其内在的观念、情感、信念系统。后者为前者作论证,前者因后者为内核而聚合起来,形成统一的人格。但是道德系统本身必须是开放的,因为道德系统本身有时不能说明自身。比如一个人之所以选择某种具体的道德行为,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公正”的。可是何为公正?为什么一个人非要按照公正原则去生活?如此提问下去,非涉及一个人的终极价值抉择与信念不可。所以道德人格内核之中仍有内核,这一内核即是他的终极价值系统——“信仰”。
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曾经指出:“每个人无论他是否有宗教倾向,都有自己最终的假定前提。”这些前提“都对属于他们的所有行为产生了创造性的压力”[1]。所谓“最终的假定前提”即是终极信仰,所谓“创造性压力”即论证、聚合等作用也。古代中国天理对人伦的持久佐证,现代中国共产主义信仰对道德人格的巨大动力作用,都证明特定的信仰系统可以支撑特定的道德人格。 [1] 赫根汉著:《人格心理学导论》(中译本),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
何谓“圣化与提升”?所谓圣化与提升的意义有二,第一是因为信仰系统的存在,道德行为本身会变得神圣起来,最高理想可以提升现实人格的境界和心理感受。禅宗讲“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相信某种“妙道”的人,相信其“担水砍柴”的日常之举都是践行“道”理的。所以,即便是担水砍柴也会显得神圣起来。基督教讲人与上帝沟通会分享“神恩”,也是由于信仰机制使然。人有了某种最高理想,或宗教,或政治,或人生,不仅会有一系列行为及其组合的动机,而且会有这一动机的增强或放大机制(如使命感、庄严感等等)。这种动机的增强与放大就是信仰予人的“圣化”或“提升”。
第二是人格形象上的提升。所有的信仰体系都会产生出相应的理想人格。宗教讲的基督、真主、佛陀,共产主义信仰体系中为这一理想而献身的英雄人物以及未来“自由王国”里的“全面发展的人”等等,都属于理想人格。这种最高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作用中的中介是个体的“理想自我”。这里存在着一个“理想人格——理想自我——现实自我”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前者对后者的不断的水平“提升”关系。也存在着伴随着这一提升的主体神圣感受问题(因为每一次提升都是离终极价值目标更近一步)。所以个体有无真实的健康的信仰系统,的确关系到道德人格建设的根基。
以上讨论的是一般人格修养的规律。实际上作为职业道德范畴的教师人格的建设也必须服从这一规律,或规律性的策略。教师要成功进行自己的人格修养,必须在两个层面上采取“取法乎上”的策略。一是在人生层面努力确立自己的终极价值体系和生活与人格的理想;二是要充分认识教育事业的神圣价值,努力确立自己的职业理想。只有形成了真正的教师人格理想,并时时与自己的现实人格相对照,找到差距、缩小差距,真正的教师道德人格修养才能成为现实。同时,也只有从大处着眼,教师才能安贫乐道,专心从事自己的事业。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第斯多惠所说的:“教育者和教师必须在他自身和在自己的使命中找到真正的最强烈的刺激;对他来说,把自我教育作为他终身的任务乃是一种双重的和三重的神圣责任。”[1] [1] 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们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341页。
2.师范人格的特点(格位高) 教师道德人格之所以必须具有较高的格位特性,理由主要有二:首先,就道德人格而言,教师必须在人格上高于一般人才具有教育的主体资格。因为只有高于一般才足以供人效法。正如第斯多惠所言“谁要是自己还没有发展、培养和教育好,他就不能发展、培养和教育别人。”其次,也只有具有较高人格品位的教师才可能获得教育对象的尊重,为学生所景仰,从而获得应有的教育效果。一般人可以不象教师那样过多地考虑人格的教育工具作用,但教师则不然。教师的工作是教育,他不能置教育效果于不顾地对待自己的人格水平和人格建设。
既然从教育事业或教师的职业要求的角度,教师必须具备较高格位的人格,在修养上“取法乎上”的策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3.中国古代的伦理智慧 这里所谓的中国古代的伦理智慧指的是“学为圣贤”的修养策略。这一伦理智慧的具体思路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无论儒家、道家或墨家,虽然理想人格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承认圣人的存在,并且不断将圣人塑造成为一个完美无瑕、令人向往的崇高、理想的人格。 第二,在中国文化中,圣贤或理想人格有神圣性却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纯粹的神。古人一直强调“圣人与我同类”的思想。 第三,由于“满街都是圣人”,所以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就成为人格修养上的必然要求。
第一,无论儒家、道家或墨家,虽然理想人格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承认圣人的存在,并且不断将圣人塑造成为一个完美无瑕、令人向往的崇高、理想的人格。 《中庸》对“圣人”的解释为:“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正因是为有了这种才德完备、富有魅力的理想人格才有了足够吸引亿兆士子孜孜以求的持久动力。例如司马迁就曾在《孔子世家》中坦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第二,在中国文化中,圣贤或理想人格有神圣性却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纯粹的神。古人一直强调“圣人与我同类”的思想。 《孟子·告子上》中以种麦为例说:同一批麦种下去,收获时有所差异,只是土地肥沃程度和人力不济所至,并非本质上有什么区别。“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圣于人而疑之”。因此,“圣人与我同类”。荀子也说“涂之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1]。所以“涂之人可以为禹”[2]。及至王阳明等人,更出“满街都是圣人”[3]的惊人之语。 [1] 《荀子·儒效》 [2] 《荀子》性恶》 [3] 王守仁:《传习录》卷下。
由于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历史人物本身是真实的存在,又由于儒家将圣人神圣化的同时一再强调圣人与我同类的特质,所以儒家的圣贤人格就具有可以趋近的特质。儒家系统内的人对此亦充满自信。比如清代陆世仪对佛、道流行的状况表示不满时即说过:“今人好学佛、学仙,而不好学圣人,不知圣贤大学之道也。未尝见人立地成佛而欲立地成佛,未尝见人白日升天而欲白日升天,明明地放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决不肯明德、新民、止至善,此之谓大惑!”[1]这就使圣贤人格不仅完美而且可以学而至之,所以“学为圣贤”就成为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个体的必然追求。所以 “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2] [1] 陆世仪:《思辨辑要》卷一《大学类》 [2] 《朱子语类》卷八。
沿着上述思路,中国古代文化(这里讲的主要是儒家学派)在人格修养上作出的贡献集中表现在下面两点上。 第三,由于“满街都是圣人”,所以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1]就成为人格修养上的必然要求。为此,中国文化中产生了丰富的人格修养的具体方法,同时教育制度也为学子们“学为圣贤”的学习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科举制度等是否真正作到了这一点,又当别论)。 沿着上述思路,中国古代文化(这里讲的主要是儒家学派)在人格修养上作出的贡献集中表现在下面两点上。 [1] 《论语·里仁》
其一,许多思想家都强调立志对于人格修养的意义,或者说人们将圣贤人格所谓修养的最终目标。比如朱熹就说 “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而今人贪利禄不贪道义,要作贵人不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1]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末有不本于志者”“ 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2]“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并不是说只要立志就够了;或者,真的立志为圣贤的就一定会成为圣贤。甚至孔子也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说“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3]。古人的真实策略是“取法乎上得其中”,即便不能成为圣贤,在人格修养上至少已有方向,而且会在实际的人格上朝圣贤的方向逐步趋近。这才是取法乎上策略的智慧所在! [1] 朱熹:《性理精义》卷七。 [2] 王守仁:《教条示龙场诸生》 [3] 《论语·述而》
其二,有了圣贤人格作为终极目标,学问无止境,修身亦无止境。这是终极目标的优越性。但是正如圣人如果与凡人无所联系,则人们只能供奉不能效法一样,在学为圣贤的总目标下,如不对目标进行分层,则跨度太大,就会使总目标抽象化、虚无化,最终失其修养与教育的效能。所以儒家从先秦直到明清,不断设计和完善了成圣成贤的分层目标,或者说他们为圣贤人格的趋近设计了中介性的人格。
一般认为,儒家认为趋近于圣贤的人格台阶为:士、君子、圣人。孔子最早作了这种人格层次上的划分:“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荀子曰:“学恶乎始?恶乎终?……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1]。又言:“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圣王”、“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 [2]。汉贾谊则言:“守道者谓之士,乐道者谓之君子。知道者为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明且贤,此谓圣人”[3]。所以从总体上言,圣人是终极的理想人格标准,君子是现实的最高人格标准,而士则为古代德育培养的一般标准也。达不到圣人、君子的水平的人,不妨首先从学习为“士”开始。由于修身与德育的最切近处是“士”,儒家对“士”的这一人格层次十分重视。
朱熹说过:“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此言知所以为士,则知所以为圣人矣”[4]。《论语·子路》中孔子也曾对子贡详细地谈到过“士”的标准:“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铿铿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论语》中对君子人格亦多有论述,如“君子周而不比”[5]、“君子喻于义”[6]、“君子成人之美”[7] “君子固穷”[8]等等。《中庸》说“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其君子的标准显然在道德人格上要求更高。古人的思路是,做不了圣贤,不妨先从做君子、做士开始。 [1] 《荀子·劝学》 [2] 《荀子·儒效》 [3] 《新术·道术》 [4] 《朱子大全》卷七十四《杂著·策问》 [5] 《论语·为政》 [6] 《论语·里仁》 [7] 《论语·颜渊》 [8] 《论语·卫灵公》
所以,从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的伦理智慧的角度出发,我们也不难理解在教师的人格建设中为什么要采取“取法乎上”的修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