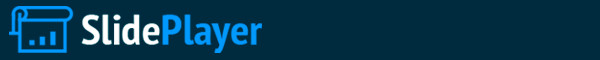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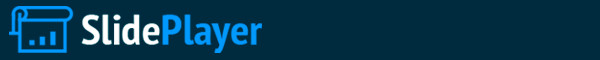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墨子與墨家哲學
墨子(約公元前480–前393),名翟,魯國人,生活在戰國初年。 他創立了墨家學派,該派和儒家在戰國時並稱為當世的顯學。在戰國中期,該學派內部發生分裂,實力嚴重削弱。到了秦漢之交,墨家作為一個學派,已徹底中斷。 學者通常把分裂前後的墨家稱為「前期墨家」和「後期墨家」。 《墨子》一書,現存53篇,是墨家的一部著作總集,內容分為三組:1.《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和《小取》等6篇,主要討論邏輯和科學問題,屬後期墨家的作品。2.《備城門》以下11篇,記載和說明墨家的防御技術和器械。3.其餘36篇則直接與墨子本人的言論和活動有關,是研究墨子思想的主要依據。 可參考李漁叔的《墨子今註今譯》(台灣商務,1974)。
一 價值觀──「兼相愛、交相利」 「兼愛」是墨子哲學的核心觀念,是墨家的主要標誌。 一 價值觀──「兼相愛、交相利」 「兼愛」是墨子哲學的核心觀念,是墨家的主要標誌。 墨子曾說「兼即仁矣、義矣」(《墨子.兼愛下》)「仁,體愛也」(《墨子.經上》),其說似近於儒家,但實際上卻有不同: 1. /儒家-仁義有親疏之別(差等/殊別之愛) \墨子-兼愛無親疏之別(平等/普泛之愛) 2. /儒家-仁義的基礎在於道德本心(義先利後) \墨子-兼愛的基礎在於功利(義利合一)
I 兼愛是一種無差別的、平等的愛 儒家所講的仁義之愛可說是一種差等之愛,這是基於現實層面來講:本心雖有普遍性,但其落實卻有特殊性,因實現時人的情感和心理發展傾向於一種差等的愛-愛親人較優先也較深厚。 ∴孔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孟子也說:「親親,仁也。」(《孟子.告子上》),又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強調由親及疏、推己及人之愛。 墨子較重視的卻是愛的最高理想,∴強調無差別的、平等的愛: 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 為人之國,若為其國……為人之都,若為其都……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墨子.兼愛》下)
他猛烈攻擊儒家所講的等差之愛,並視為出於人的自私自利的心: 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墨子.兼愛》上) ∴他提出「兼以易別」(《墨子.兼愛》上)的主張,即以兼愛取代差等之愛。他甚至主張愛應反儒家之道而實行: 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墨子.兼愛》下) 先愛別人的親人,則別人也會愛我們的親人。
講者評論:墨子的兼愛的觀點是正確的,但與儒家的差等之愛並無根本的衝突,∵兩者的層面(理想與現實的層面)不同。→其批評儒家的差別之愛是偏而不全的,其主張愛陌生人而使後者投桃報李的觀點不合情理,亦難以落實。 另外,其實儒家雖強調等差之愛,但卻並沒有放棄最後的理想是普泛的愛,如孔子曾說:「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唐代韓愈更說:「博愛之謂仁。」(《原道》);這種觀點較墨家周備。
II 兼愛的基礎在於功利 儒家講仁義,是以道德本心為基礎的,而不是外在的事物為基礎,∴一方面強調仁義內在。另一方面,又主張義利之辨。如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孟子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案:儒家講義利之辨,並非排斥利益,如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 →是一種義先利後的主張。
墨子講兼愛的意義卻是指利益,∴愛與利常連用,說:「兼相愛、交相利」(見《兼愛》中、《兼愛》下、《天志》上等篇)。如說: 既以非之〔案:指反對人自利而不相愛〕,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愛》中) 後來,墨子後學更以利來說明墨子所講的「愛」的意義: 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墨子.經說上》) 這裏除了以利來說明愛(仁義)外,亦說明愛並無內外之別。
他所講的利是指利他而非利己之利。i.e.大眾利益或即功利(utility)。 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今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墨子.兼愛》下) →其觀點與西方功利主義非常接近:功利是道德原則的終極標準。 講者評論: 1. 墨子及西方的功利主義者在倫理學上有相同的困難: a. 無法解釋超利害的道德行為。 b. 導致違反明顯的一般道德原則的行為。
2. 儒家所講義利之辨,雖只是一種義先利後而非排斥利益的主張,但卻將利益視為非道德(non-moral),即與道德不相干,這與我們對大眾利益的道德反省不符。∵道德與功利有很大的親和性。 →我們可以把功利原則吸納於儒家倫理學中,將它看成中層的原則。i.e.道德原則可以分開三層: /最底層-是一般的道德原則。 -中層-是功利原則與非功利原則。 \最高層-是終極的道德原則,可稱為仁義原則。 i.e.一般道德原則可以用功利原則和非功利原則來決定,但當此二原則有衝突時,則以更高層的仁義原則來決定。
二 天道觀──「天志」、「非命」 I 「天志」的觀念 墨子雖以功利作為道德的終極標準,但他卻又同時以天志為道德的終極標。 二 天道觀──「天志」、「非命」 I 「天志」的觀念 墨子雖以功利作為道德的終極標準,但他卻又同時以天志為道德的終極標。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墨子.天志》上) →終極的道德原則有二:功利與天志 其「天志」有類基督教所講的神,是一有人格意志的形上實體:
1.天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 若毫之末,莫非天之所為也,而民得而立之,則可謂厚矣。」(《墨子.天志》中) 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宮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墨子.天志》中) 世界上所有事物,包括極微小的東西都是天所創造的。
2.天是全知全能的 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己矣。(《墨子.天志》中) 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而得罪,將惡逃避之?曰:無所逃避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間無人,明必見之。(《墨子.天志》上) 世界上所有事物天都能知道,∴人獲罪於天,便無法藏身逃避。
3.天是全善的,並且能賞善罰惡 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墨子.天志》上) 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墨子.天志》下) 天的賞善罰惡,連天子(君主)也不能倖免。
墨子雖然以為道德的終極標準有二,但並不以為因此會有衝突,∵天的善惡標準,亦在於功利(兼愛交利): 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墨子.天志》下) →功利與天志在價值上完全統一。 →墨子所講的天志雖與基督教所講的上帝在作為創造者及具人格意志方面相同,但其以功利作為價值的最高標準,則並不相同。 另外,墨子與基督教將價值的最終根源了解為具人格意志的形上實體,這與儒家所講的天道的人格意志意味淡薄不同。
II 「非命」的觀念 墨子的「非命」的觀念,旨在反對命定論或即宿命論;後者指人的一切行為由命運所決定。墨子以為這種觀點出於儒家,並加以批判: 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墨子.非命》上) 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吏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墨子.非儒》上)
針對執有命者的觀點,消極來說,墨子主張非命──否定命運,積極來說,他主張「強」和不敢怠倦: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 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粱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賞,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 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術藝,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
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墨子.非命》下) 「強」指勤力工作,各段意思指全國國民努力與命運周旋,從而戰勝命運,這樣,國家才得以富強和穩定。 以下,我們進而討論墨子在命的問題上對儒家的批評是否正確。儒家確有人有命限之義: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論語.顏淵》)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有斯疾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論語.雍也》)
然而,儒家說命運、命限時,並非持命定論觀點,而是一種義命分立的觀點。i. e 子路曰:「不士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衛子》)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盡心》上) /自然世界-具必然性,無自由可言 \價值世界-有自由可言 →儒家講命,並非命定論,∵亦講人的自由。而且,比墨子講非命更合理,∵生死、富貴之事,確非人力所能完全主宰。
另外,儒家更有即命顯義之說,此義亦非墨子所能及: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論語.憲問》)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盡心》上) 孔子所說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孟子所說的「立命」,都是指無論人的命限如何,都必須以義承擔,此為即命顯義的觀點,此觀點比義命分立說更進一步,指出義與命兩者可有相即不離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