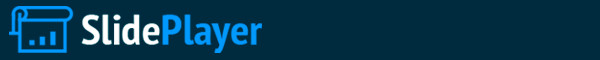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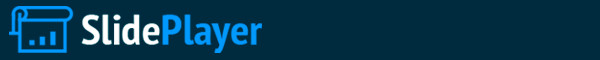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你為什麼要寫詩? 主講人:向 明 送詩人進社區
沈澤宜 (詩人、北大才子、文學教授。曾為一首詩被關十二年) 他說:作為文學之魂、人類靈魂的詩歌, 它像光一樣流動、火一樣明亮,風一樣自由。 是烏叫、晚鐘、嬰兒哭泣, 引領在物欲場中走失的靈 魂重新找到歸家之路, 詩讓人變得善良、高尚、寬宏大量。 一完整的世界、 詩人永恆的訴求是為了讓世界完整起來, 儘管這有點像夸父追日, 精衛填海、西緒岪司推石上山、 但這總比眼睜睜看著它破碎, 甚至於與它破壞的進程要好。
彩羽 (詩人、退伍軍人、收過破爛、擺過地攤、當過副刊編輯) 他說:詩人、是一個名字。上帝,也是一個名字, 然而在這兩個名字之間,又有什么分別呢? 他們的雙肩都承坦著天國的光榮, 各有其色彩、各有其光輪, 且他們都是真理火炬的製造者。
張慶和 (大陸青年詩人)說 〈詩人是一棵草〉 不用播種 不必水澆 其實 詩人不過是一棵草 是生是滅 是枯是榮 全憑自己的那靈性 種上草坪的 便被重用 遺忘路邊的 是自由生命 想踩的,就由他去踩吧 想燒的,就任他去燒吧 應天而來 順時而去 誰在乎風雨抽打 去葉除根 張慶和 (大陸青年詩人)說 〈詩人是一棵草〉
路也 (大陸新生代女詩人,曾獲第三屆中文青年詩人首獎) 她說:我是因為生活而寫詩的。 寫詩對我來說、已經是一種毛病, 是我生活中的部份了, 跟功成名就、跟流派, 甚至跟寫作的抱負都沒關係, 它就像女人做針線活一樣, 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了。 這與我個人的生命狀態有關。 我不相信那種過份機巧的詩歌, 像生產線上製造出來的機器零件一樣, 我是一個天生的自由主義者和本能的理主義者, 我常常感到我的身体裡蘊藏巨大的能量, 對世俗生活充滿了過份的熱情, 正是這些特質使我不斷的寫詩。
韓少君 (大陸中生代名詩人,曾獲長江文藝獎詩首獎) 說:我堅信思考永遠大於寫作, 這個世界與事物之間的關係, 正發生各種變化, 詩人其實就是這些細微關係的記錄者, 他存在的价值就在所謂物質文明不斷擄掠 我們的今天、為了保留住我們與客觀存在 建立的最柔軟、最敏感的關係, 詩歌是我們與這世界保留的擦痕。
嶈子龍 (大陸名詩人,在2005年(春天送你一首詩)的活動題句) 春天太短了 格外 需要詩的滋養
周夢蝶 (台灣現代詩壇的泰斗,現年86歲,從前在武昌街明星麵包店門口擺舊書攤,現在也是靠老兵加給過日子)有詩〈詩與創造〉道出詩人的位置: 上帝己經死了。尼采問 取而代之的是誰? 「詩人」 水仙花的鬼魂 王爾德忙不迭的接口說。 不知道誰是誰的哥弟? 上帝與詩人本一母同胞生: 一般的手眼,一般的光環 看誰更巍峨更謙虛 誰樂於坐誰的右邊
小蝶 (女詩人,現居台南縣關廟鄉,為托兒所的媬姆)她是這樣的〈說詩〉: 這條路人煙稀少 寂寞的詩 還在緬懷 盛唐李杜的風釆 這是五花八門的年代 功利蟹行 聲色成為標靶 一路上盡是競遂的人潮 閒情己死 無處容身的詩 很 瘦
向明 (在下我、一個「小康水平」的詩人)在今年的「國際詩人筆會」 題於國際詩碑上的一首極短詩, 題目就叫〈詩人〉: 詩人挺立如樹 總是、風來葉擋 雪壓枝撐 腳步,半寸也不挪移
法國詩人 班納德 洛林(Bernard Lorraine 1932) 曾經在被問到〈怎樣才能成為一個詩人?〉寫下下面的詩句作答: 您最好去請教大風,問它為什麼嘯鳴。 請教大地,問它為什麼震動。 請教海洋,問它為什麼波濤洶湧。 或者去請教火山,問它如何精心籌劃自己的岩溶。 即使你給我帶來了它們的答案 而我,還是不知道如何將這個謎底猜中。
向明 (我在1975年四月曾寫過一首詩〈瘤〉:這是我追求詩的心得) 你是潛藏於体內的 欲除之而後快的 那一種瘤 是一種久年無法去除的 絕症 除了灰飛煙滅 你絕不止於過敏於花粉 夏秋間 一隻蟬脫蛻時的痙攣 你也痙攣
而且,你頑固如掌上的一枚繭 剝去一層 另一層 又己懷孕 我吸取天地之精華 你吸取我 我口含閃電 你發出雷鳴 我胸中藏火 你燃之成燈 最後,你無非是 要把我瘦成一張薄薄的紙 紙上的一些什麼 凡掃過的日月 競相含淚驚呼 這才是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