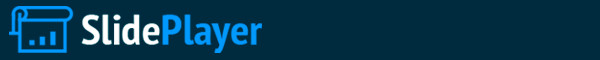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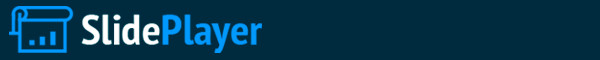
第五講 中國領導的特色(三) 授課教師:何世同博士/將軍
以統御為主軸的兵家領導戰略思想 一、孫子兵法 二、吳子 三、孫臏兵法 四、司馬法 五、尉繚子 六、六韜 七、三略
「兵家」,可以說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之間交相 征伐的產物,雖未入春秋諸子「九流十家」之列,但 歷朝歷代論軍議戰者眾,故「兵家」輩出,傳世「兵 書」豐沛,對後世之領導,影響很大。 尤其是,前述「九流十家」對領導議題論述的重心 ,多放在理論、心靈與哲學層次,有時甚至成為高深 學問,難以理解與施行。 但「兵家」不然,談理論之外,也談實踐與實用層 次之事務,道理較簡單,蘊含管理概念,易懂易行, 能結合實作,而常為「將帥領導」所採用,形成中國 領導的另一大特色。
《漢書‧藝文志》載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 職,王官之武備也。」並概分其項目為四: 一、「兵權謀」類 二、「兵形勢」類 三、「(兵)陰陽」類 四、「兵技巧」類。 其中的「兵陰陽」,專論天時、陰陽、五行之變,並 夾雜鬼神迷信,今已少人再論。 「兵技巧」,主研攻守器械之巧,則隨文明的進步, 軍事科技的發達,也無用於今世。 「兵形勢」,主談兵勢變化,其概念或與現今看法有 共通之處,惟所列「兵書」,除《尉繚》外,所存無幾 ,故亦無足論。
唯有「兵權謀」類,傳世之書最多,歷久而彌新, 這些「兵書」包含之範圍甚廣,它們不但是歷朝歷代 練兵、帶兵、用兵的準則,也是治軍與培養指揮氣度 的寶典,更是戰略思想與行動之搖籃,以及指導戰爭 之理論基礎和原動力量;歷代的英君名將,無一不接 受其哺育。 而其特色之一,就是一些「兵學」思想家對「將帥 修養」與「指揮藝術」的重視,從而提出了許多以軍 隊「統御」為主軸的「領導理論」;《孫子兵法》即 是其代表。
不過,中國之「兵學」,雖盛極於二千餘年前的春 秋戰國時期,並長期致用於秦、漢以迄元、明、清初 ,但卻衰退於近世,此政治昏聵下的人謀不臧所致, 無損於中國「兵學」之博大精深。 至於西方之「兵學」,雖早萌芽於希臘、羅馬時期 ,但卻也經過中世紀之長期停滯,一直等到十五、十 六世紀以後,隨伴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大航海時期 、工業革命、啟蒙運動、自由主義的出現,才開始興 盛茁壯,終成世界主流。 觀察西方後來居上的「兵學」發展過程,與中國之 先盛後衰相較,剛好相反。
近代西方「兵學」雖獨領風騷,成為世界主流;但 其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如:約米尼(Jomini,1779~1869) 的《戰爭藝術》(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克勞塞維茲 (Clausewitz,1780~1831)的《戰爭論》(On War)、史蒂芬(Schlieffen ,1833~1906)的《史蒂芬計畫》(Schlieffen Plan)、馬漢(Mahan, 1840~1914)的《海軍戰略論》(Naval Strategy,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 on Land) 、魯登道夫(Ludendorff,1865~1937)的《總體戰》(Total War)、 杜黑(Douhet,1869~1930)的《制空論》(The Command of the Air)、 富勒(Fuller,1878~1966)的《戰爭指導》(The Conduct of War:1789~ 1941)、以及李德哈特(Liddell Hart,1895~1970)的《戰略:間接 路線》(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等,均以戰爭理論、軍 (兵)種戰略、用兵原則為主要內容,較不涉及「領導」 領域之問題,不若中國之博大精邃。
中國之「統御領導」思想與理論,概於春秋戰國至 秦漢之際發展成熟,「成一家之言」的傳世「兵書」 ,或「兵家」之立言,除《孫子兵法》外,著名者尚 有《吳子》、《吳起》、《孫臏兵法》、《司馬法》 、《尉繚子》、《六韜》與《三略》等。 其後繼之「兵書」與「兵家」,有關領導之立言雖 多,但範圍與意境均無法超越前述諸書;要之,亦不 過在前書基礎上,取其所需,加以注釋、總結或運用 而已。 茲舉前列諸「兵書」有關領導思想與主張部分,述論 如下:
一、《孫子兵法》 本書為春秋晚期「兵家」、齊國人孫武仕吳之前所 作,共十三篇;包括:重兵慎戰、知兵知戰、戰勝不 復、因形無窮之「戰爭觀」;廟算致勝、勝兵先勝、 不戰屈人、伐謀伐交、取用於敵、機動速決的「戰略 理論」;及正合奇勝、詭道詐立、用間用火、重視地 形的「用兵藝術」。為影響中國「戰略思想」與「領 導藝術」最深遠的兵學巨著。《孫子兵法‧始計第一 》開宗明義載曰: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 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 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將者,智 、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兵」,是指「戰爭」而言。孫子認為,「戰爭」是 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國家「領導者」,應以「道、天 、地、將、法」等五件事,作為經營戰爭的基礎,並須 經過「計算」,比較敵我力量之強弱,而探索雙方優劣 之情勢。 這是孫子的「國家領導」及「國家戰略」層級的「狀 況判斷」概念。「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則是國 家「領導者」須揭櫫戰爭目的,使全民瞭解「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進而爭取全民的支持,而不畏危險 ,全力擁戴;此一上對下「綁心」,下對上「交心」的 過程,正是「溝通式領導」之最高要旨。
「將」者,「智、信、仁、勇、嚴」,則是孫子「論 將」的條件,唯有具備此五項「武德」,才足擔負艱巨 的軍隊「統御領導」重責大任。 「法」者,是指軍事制度與法規,包括:(一)「曲制 」:軍隊的編制、編組與作戰序列;(二)「官道」:軍 隊成員應遵守的營務營規、內部管理、陞遷賞罰等人事 勤務;(三)「主用」:軍費、兵器、糧彈、裝備等軍隊 所需的主要用度。 此三者必須密切配合,強力運用,始可稱為「建制」 之部隊,始能勝任作戰任務。 孫子在二千多年前,已發現編制、人事與後勤支援的 重要性,此屬「軍事管理」範疇,亦為孫子「領導思想 」的最基礎認知。
孫子曰:「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兵勢第五);「部 曲」為「分」,「什伍」為「數」。將軍隊按「分」、 「數」原則編組,建立「指揮系統」,層層節制,運籌 帷幄,此「軍隊管理」之神髓也。 此外,在孫子的認知中,「管理」的基礎,應建立在 嚴格紀律之上;平時治軍無法,律民無方,訓練不實, 戰時就不能發揮戰鬥效能;故除應「令素行以教民」(行 軍第九)外,更須因應情勢,「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九地第十一),才能「號三軍之眾,若使一人」(九地第十一), 落實領導效果。
再者,戰爭的本質殘酷;因此,孫子主張「慎戰」。 非至確實有利之時,決不採取行動;非到掌握致勝之機 ,決不用兵;非在危急存亡之際,決不言戰。目的除在 避免「亡軍亡國」的嚴重後果外,也在體恤生靈,不遭 塗炭之災;這是明主良將的「指揮道德」問題,也是以 「人」為中心的「領導思想」中,最核心的價值問題。 故而,《孫子兵法‧火攻第十二》載曰: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 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 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復 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 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在「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互動上,孫子非常重 視將帥對士卒的態度,提出「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 失眾也」之告誡。意思是,將帥對部屬說話反覆叮嚀, 嘮嘮叨叨(諄諄),而且神色不安(翕翕),這就是「失眾 」的現象,可與領導失敗劃上等號。 此外,孫子認為「獎賞」是將帥「統御領導」的法寶 ,但須適度,不可浮濫;故接著又曰: 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眾 也,不精之至也。(行軍第九)
孫子的意思是:將帥以連續獎賞方式,取寵部下, 此領導無能之反映;以連續處罰方式,樹立威信,此 領導困窘之投射。兩者均能陷將帥於被動,皆應避免 而先對待部下殘暴,致「失眾」而成亂軍,將帥反 畏怕而將就之,這更是最不懂「帶兵」與「知兵」之 道的領導失敗現象。 而為了達到「帶兵」能「服眾」之目的,「統御領 導」當須講求賞罰分明;當罰則罰,當賞則賞,文武 兼施,恩威相濟;此即孫子所曰:「卒未親附而罰之 ,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 可用」,故應「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的道理。如此 ,軍隊才能成為精練之師,用於戰場,必可取勝。 (行軍第九)
其次,將帥治軍,雖以「嚴明」為第一要義,但也須 有「愛兵如子」的認知,以剛柔調合,換得部屬「交心 」;此即孫子:「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 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地形第十)之「愛兵」主張。 但是,「愛兵」也不能毫無節制,變成溺愛,適得其 反;故孫子接著曰:「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 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地形第十);以提醒將帥 注意。 孫子又認為,在未戰之前,可以透過對五種狀況之判 斷,預知能否取勝。其中,強調將帥「帶兵」應先「帶 心」的「上下同欲」,及放手讓第一線指揮官適度「獨 斷專行」的「將能而君不御」,都是領導成功的效果投 射。(謀攻第三)
不過,在孫子的「軍事領導思想」中,也有一些不合 現今時宜的地方;例如《孫子兵法‧九地第十一》載孫 子之言,曰: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 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 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 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 之。 這是標準的「愚兵主義」。
觀察中國歷史上的將帥,多喜士卒出身農村,能刻 苦吃粗,又知識淺薄,思想簡單,只做事,不說話。 領導這些士卒,只要白天施以連續訓練或服行粗重勤 務,累其筋骨,晚上就會力盡而眠,無多餘工夫玩耍 花樣,而唯將帥之命是從,有如羊之被驅。 老師認為,這種傳統中國「窮兵」、「累兵」、「愚 兵」的帶兵模式,若上探源頭,多少應受到孫子「驅羊 論」之推波助瀾影響。但在兩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中, 這恐怕也是很正常的現象;瑕不掩瑜,並無損其整體思 想的偉大精深。
二、《吳子》 《吳子》,又稱《吳起》、《吳子兵法》、《吳起 兵法》,傳為戰國初期吳起(?~前381)所著,是吳起 與魏文侯、武侯論兵對談之記錄;今本有圖國、料敵 、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是繼《孫子兵法》 之後,又一部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先秦「兵書」。 《吳子》與《孫子兵法》向來相提並論,被奉為「 兵學」經典,是戰國後期家戶必藏之書。(韓非子‧五蠹) 司馬遷《史記》,將孫吳同列一傳,曰:「世俗所稱 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史記‧孫 子吳起列傳)即是。 《漢書‧刑法志》論天下「兵家」,亦曰:「吳有 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 ,垂著篇籍。」可見《吳子》一書的歷史地位。
若以孫子、吳起兩者相較,吳書以「正」,似《論 語》;孫書以「奇」,似《孟子》;(宋‧羅大經《鶴林玉 露》甲篇卷2)思想一以貫之,但各有特色。 吳起的領導思想,大體站在君王立場,對「治國」、 「論將」與「治軍」等方面,提出見解。 在「治國」方面,吳起認為「國家領導」的基本概念 ,就是「內脩文德,外治武備」;《吳子‧圖國第一》 載曰: 昔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 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 脩文德,外治武備。
《尚書‧甘誓》有載:「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 故「有扈氏」是夏初的一個「部落聯盟」(或曰「方 國」);而「承桑氏」亦可能是其前後時期的另一個 「部落聯盟」。 吳起以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有扈氏之君「恃 眾好勇」,俱遭滅國之禍為例,提醒魏文侯,「國家 領導」之道,一方面應「內脩文德」,以教化人民, 增強全民道德意識;另一方面,亦應「外治武備」, 以建軍備戰,防敵侵犯。兩者須雙管齊下,才能確保 國家安全。 吳起既強調「治國」之基礎,在於「文德」與「武 備」兼具,而將帥身繫國家安危重擔,因此「論將」 就不能僅放在「勇」上。
「勇」只是條件之一,所以必須選取「文武兼備、 智勇雙全」者,求其「均衡性」,才能上下連貫,落 實君王的「治國方略」;《吳子‧論將第四》載曰: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 。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 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 戒,五曰約。 依照吳起的解釋:「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 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 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吳子‧論將第四)
而將帥除須做到上述「五慎」之外,更須知「氣機、 地機、事機、力機」等用兵之機,方可成為「得之國強 ,去之國亡」的「良將」。(吳子‧論將第四) 其實,上述的「五慎」、「四機」,很大一部分屬於 「軍事管理」的範疇;這可能就是論者以「吳書以正」 的原因。 吳起的「軍事管理」概念,還用於「治軍」之上。吳 起認為,軍隊的編組,須以士卒的專長與特質為依據, 「聚為一卒」;有了這樣的「戰鬥編組」,就可以成為 「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的精銳勁旅。(吳子‧ 圖國第一)
吳起又認為,軍隊致勝的關鍵,在素質,不在數量, 而強化素質的工夫,就在「治」上;《吳子‧治兵第 三》載曰: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 問曰:不在眾乎?對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 金之不止,皷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 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 可追…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不過,再好的「治軍」方法,也必須以嚴格的訓練為 基礎,才能達到「父子之兵」的戰力標準。故吳起的「 用兵之法」,強調「教戒為先」,採取類似今日「多層 次直銷」的「幾何級術」概念:「一人學戰,教成十人 ;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 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吳子‧治兵第三)
此外,吳子的「軍事管理」思想也用於「教戰之 令」上,又曰: 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 旌旗,勇者持金皷,弱者給廝役,智者為謀。 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皷整兵,二皷習陣, 三皷趨食,四皷嚴辦,五皷就行…(吳子‧治兵第三) 吳起認為,將帥必須根據軍隊成員的特點與背景, 賦於適當的戰鬥、勤務或參謀任務,並將同鄉里、同 什伍的人編組在一起,以鼓聲統一作息行止,才能發 揮最大戰力;這些都是「統御領導」的本務與基礎工 作。 吳起在兩千多年前,就有這樣合乎科學的「軍事管 理」觀念,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三、《孫臏兵法》 又稱《齊孫子》,為戰國中期孫臏受刑後的論兵之作 文志》著錄八十九篇、圖四卷,但已不見於《隋書‧經 (「臏」,古代削去膝蓋骨之刑罰也;故此孫子,即孫臏);《漢書‧藝 文志》著錄八十九篇、圖四卷,但已不見於《隋書‧經 籍志》中,判斷原書在東漢至隋之間已佚失。 直到1972年,大陸考古學者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挖 掘中,出土《孫臏兵法》殘簡364枚,約有11000字,經 整理編為三十篇,才使這篇失傳千餘年的偉大先秦時期 「兵學著作」,得以重見天日。 此一「地下史料」,也旁證了孫子與吳起「兵書」的 真實性。更難得的是,孫臏的「兵學」思想,曾經透過 「桂陵」與「馬陵」兩次戰役的驗證,創造了「圍魏救 趙」與「增兵減竈」的用兵範例,是一位「理論」與「 實踐」結合的一代「兵學大師」。
孫臏曰:「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孫臏兵法‧見威王) ;他和孫子、吳起一樣,都重視戰爭的勝敗,但孫臏更 具有以「權力」概念為主軸的「現實主義」思想。 孫臏強調,在戰爭及君王施政中,沒有比「人」更可 貴的東西,故有「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孫臏兵法‧ 月戰)之言。而「人」既可貴,為了贏得戰爭勝利,建軍 重心,就得放在「人」素質之上;《孫臏兵法‧篡卒》 載曰: 兵之勝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勢,其 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歸,其強在 於休民,其傷在于數戰。 「篡卒」,就是「挑選士卒」之意。唯有注意上述八 項事情,君王或將帥才能獲得士卒的擁護,而贏取戰爭 勝利。
而除了「篡卒」之外,孫臏更注重對將帥的選拔,提 出「信、忠、敢」的明確條件。 「信」,就是「信賞」;「敢」,就是「敢去不善」 ;「忠」,就是「忠君」。(孫臏兵法‧篡卒)也就是說,作 為一名將帥,必須信賞明罰,敢於改正錯誤,去除不良 習性,以及效忠自己的君王,否則就得不到部屬的敬重 與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在孫臏的「統御領導」思想中,強調 了孫子、吳起所無的「忠君」概念。孫臏歸納戰爭勝與 不勝的原因,曰: 恒勝有五:得主專制,勝;知道,勝;得眾, 勝;左右合,勝;糧適計險,勝…恒不勝有五 :御將,不勝;不知道,不勝;乖將,不勝; 不用間,不勝;不得眾,不勝。(孫臏兵法‧篡卒)
其中,「主專」、「御將」、「乖將」、「得眾」、 「左右合」等觀點,都應是孫子「統御領導」思想的延 伸,無足再論。 較有特點的是,孫臏以「矢弩」的結構與發射原理, 將士卒、將帥、君王,比喻成矢(箭)、弩(弓)、射手, 進一步論述君王、將帥與士卒的互動角色,也反映了他 的「統御領導」基本概念。 孫臏認為,士卒的編組,猶如箭的構造,唯有「金在 前,羽在後」的「前重後輕」設計,才能射中目標。 將帥的指揮,就像弩的原理,兩臂平正使力,引張弩 弦方法正確,才能有效發射;君王的決策,則好比射手 的技巧。必須三位一體,同心協力,才能贏得戰爭勝利 。此即孫臏所曰:「兵之適(勝)敵也,不異於弩之中招 也」的道理。(孫臏兵法‧兵情)
四、《司馬法》 成書於戰國中期,乃齊威王仿效春秋晚期齊國名將司 馬穰苴用兵,命大夫追論其兵法,附穰苴於其中,是一 部官修「兵書」;司馬遷譽之為「閎廓深遠,雖三代征 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史記‧司馬穰苴列傳)。 其思想主軸,在強調「以仁為本,以義治之」(司馬法‧ 人本第一) ,主張「以戰止戰」(司馬法‧人本第一) ;其所曰: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人 本第一),更是千古警世之言。 《司馬法》認為,古時候王者的「治國」與「興兵」 ,都會遵循「仁、義、禮、信、智、勇」等「六德」, 以教民、理軍;並在戰爭準備上,提出「順天、阜財、 懌眾、利地、右兵」的「五慮」要求。(司馬法‧定爵第三)
而一切無慮後,才能去和敵人作戰;這是一種戰爭前 以「安全」為考量的「狀況判斷」概念,與《孫子兵法 ‧始計第一》所揭櫫之「廟算」觀念略同。 此外,將帥「統御領導」的才能,應表現在作戰指揮 之上,如此才能「服眾」,才能贏得勝利;因此,其對 將帥要求的標準是「完美化」,將帥不但須有孫子「智 信仁勇嚴」的條件,更要有「定靜安慮」的修養,以及 「親兵」、「愛兵」的工夫,能與士卒同甘苦、共患難 。(司馬法‧定爵第三) 司馬法非常重視國君與將帥「統御領導」內外在作為 的融合,他認為:領導者平時治國要注意恩惠與信用, 創造和諧環境;帶兵要威武有豪氣,維護嚴明軍紀;作 戰要勇敢而敏捷,並保持冷靜思維。
一個國君與將帥,唯有做到以上要求,才能成為在國 家有好名聲、在軍隊是好楷模、作戰時受部屬信賴的好 領導者;當然,有了這樣的領導者,就可以取得戰爭勝 利。 此外司馬法也強調「賞罰」的重要性,其原則是「公 正適當」、「從重從快」,以收宣教目的;故曰:「賞 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 不善之害也。」(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 司馬法又認為,將帥不可但憑一己好惡私念,而濫施 賞罰;否則就是「專權」。而在作戰過程中,領導者除 應「重賞罰」外,尤須:戰勝時「與眾分善」,戰不勝 時「取過于己」,再戰時「誓以居前」。(司馬法‧嚴位第四)
不過,「賞」與「罰」之間,司馬法似乎更重「罰」 ,認為「嚴罰」具有警惕作用,使人不敢犯法;故有「 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的主張。(司馬法‧嚴位第四) 總之,老師觀察所見,司馬法領導概念的最大特點, 在於具有較強的「整體感」,與向下紮根的「務實感」 ;此與同一時期以「理論見長」的孫子、吳子、孫臏等 人相比,層次與內涵均有不同,但具互補作用。
五、《尉繚子》 成書於戰國中期,出於梁惠王時尉繚之手(隋書‧經藉 《尉繚子》崇尚「法治」,具濃厚的法家思想,亦有 三)。 《尉繚子》崇尚「法治」,具濃厚的法家思想,亦有 較強的兼容性;其開宗明義第一篇,就談「天官」問題 ,標示其「無神」看法。 所謂的「天官」,就是古時候對天體星象的總稱,以 此推算陰陽時日的向背變化,決定人世間的凶吉,也用 於預測戰爭的勝敗。但尉繚不同意這種觀點,在與梁惠 王對談時,曰: 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 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城者,城高 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 若城下池淺,守若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 時日,不若人事也。(尉繚子‧天官第一)
尉繚認為,唯有「人事」,才是戰爭的主體與勝負的 主宰者,和「天官時日」並無關連。比如攻城,若東西 南北都無法攻破,難道這四個方面都沒有適於破城的「 良辰吉時」嗎?其實攻城成敗的關鍵,在雙方「人為」 的作戰準備,而不在將帥對「天官時日」的迷信。 為將者,必須有「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 於人」(尉繚子‧武議第八)的氣魄與修養;這樣將帥領導士卒 、指揮作戰時,才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 ,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 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尉繚子‧兵談第二) 因此,尉繚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 人所貴,人事而已」(尉繚子‧威戰第四)的見解,此觀點與孟 子相同。
尉繚認為,將帥與士卒間的互動,應以「誠」為基 礎。 (尉繚子‧攻權) 尉繚對王者與將帥又有「不私於一 人」(尉繚子‧攻權)的期許,認為唯有領導者「使民無私 」,才能「天下一家」。(尉繚子‧治本) 《尉繚子》崇尚「法治」,強調「武禁文賞」(尉繚子 ‧治本),著重「軍事管理」;以全書的一半篇章(篇十 三至篇二十四),詳述與「統御領導」基礎工程相關的 「軍事法令」條目。 總而論之,老師認為,尉繚不僅是一代「兵學宗師」 ,更是一位古典「理性」兼「現實」主義的思想家;其 能在當時打破神權與封建禁錮,出現「注重人事,不求 鬼神」的「無神」思維,尤其難得。
六、《六韜》 或稱《太公六韜》,約成書於戰國後期,托名於齊太 公姜望(即姜牙或呂望);包括文、武、龍、虎、豹、犬 等六韜,故名。全書共六十篇,惟部分內容已佚。 《六韜》之政治思想,首論「君道」;「君道」,也 就是「國家領導」之道。作者以儒家思想為主,融合諸 子觀點,對君王提出「仁」、「德」、「義」、「道」 修養的要求。(六韜‧文韜‧文師第一) 《六韜》主張「天下為公」,「唯有道者處之」(六韜‧ 武韜‧順啟)。其「國家領導」思想,認為國君須與人民共 享天下利益,才能得到天下;若獨享天下利益,就會失 去天下。只有不掠奪人民利益者,才能獲得人民擁戴。 (六韜‧武韜‧啟發第十三)
七、《三略》 《六韜》對將帥修養的要求很高,希望將帥都能做 到「智勇雙全」、「才德兼備」、「人格完美」與「 忠於人君」;唯有這樣條件的人,去帶兵打仗,才能 獲得全勝。 七、《三略》 又稱《黃石公三略》,或《黃石公記》。舊題黃石公 著,或稱下邳神人撰,因出於秦漢之際人物之手,偽托 姜太公所作,由黃石公受張良,故名。(史記‧留侯世家) 不過,黃石公授張良者,分明是《太公兵法》,但卻 由此流傳成為《三略》,至今無人能曉,也因此出現 《三略》成書的一些不同說法。
《三略》兼採儒、道、法、墨諸家思想,與讖緯迷 信之說,因其很多內容,講求人情世故,能與世俗人 性結合,容易深入人心,故為歷代領導實務者所推重 。 全書分上、中、下三略,是一部著重政略、心略與 修養心性,成為「帝王師」的兵書。本書作者認為, 不論為國之道,為將之道,都要體察眾心,收攬民心 ,注重民事,關心民命,更要崇禮重祿,才能收到萬 眾一心的領導效果;這是《三略》在「領導思想」上 的主體價值觀念。
在將帥修養與能力方面,《三略》引《軍讖》之言, 認為將帥應「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 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 ,能制軍權。」(三略‧上略) 也就是說,優秀的將帥,必須具有智、賢、能、勇、 仁等「均衡」條件於一身。按,《軍讖》可能成書於商 朝或更早時期,應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戰爭理論著 作;和其同時期的兵書,還有《軍勢》與《軍政》,但 均已無從考據。 《三略》進一步提醒將帥,應以公正開闊的胸襟,修 己安人,建立良好的領導風格;將帥切不可犯「拒諫」 、「策不從」、「善惡同」、「專己」、「信讒」與「 貪財」等缺失。(三略‧上略)
以上六項缺失,《三略》作者認為:「將有一,則眾 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 及國。」(三略‧上略) 此外,《三略》一方面要求將帥要有「恕己而治人, 推恩施惠」(上略)的修養,另一方面亦強調「將無威」而 「軍必喪」的概念。(上略)而維持「將威」的關鍵,就在 「軍令」與「賞罰」之上。(上略) 《三略》作者,深知人有好面子的天性,故將帥應待 士以「禮」;又知人有自私的本性,重賞之下,不止有 「勇夫」,更能招致「死士」。因此,又引《軍讖》之 言,從「人性面」論述「賞」與「禮」在「將帥領導」 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曰: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 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上略) 不過,《三略》對「將帥領導」最生動、最務實的論 述,莫過於將帥除須愛兵如子外,更要刻苦吃粗,生活 與士卒一致,以身教代替言教;甚至有樂士卒先享,有 苦自己先擔,如此才稱得上是「將」。載曰: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軍井 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灶 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揮扇,雨不 張蓋,是謂將。(三略‧上略);「醪」(音勞),古時含有 渣滓的濃酒。
《三略》道出了「人為知已者死」的最深層意義,也 是「統御領導」的最高境界。反之,如果將帥高高在上 ,將士卒看成「路人甲」,那麼士卒也必會把將帥視為 「路人乙」。 總之,對領導者而言,《三略》是一部「實用型」的 「兵書」,言簡意賅,本身沒有太大理論,多為領導實 務投射的論述。 黃石公《三略》之問世,正是秦末喪亂之際,也是黃 老思想逐漸抬頭之時,故本書受此歷史政治背景影響, 雖曰兼採儒、道、法、墨,但卻偏向黃老。 故本書自稱「衰世作」,意在期望人主(領導者)通曉 治道,安邦治民。
老師認為,本書之所以受到歷史上「兵家」的重視, 一方面應是其多引《軍讖》之言,反映了上古中國王者 治軍、治國之道;另一方面,也與黃石公以本書授張良 ,張良助劉邦平天下有關。